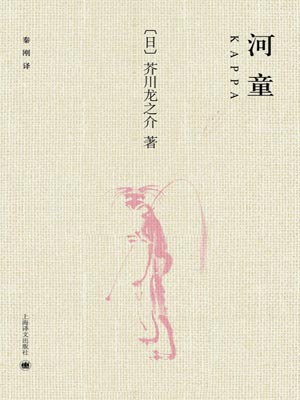迈克尔·罗伯森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社会服务部门有遭受性虐待儿童的档案。我以前可以查到这些资料,但现在我不在体制内。隐私法越发严格了。
我得找人帮忙,这个人我已经十多年没见了。她叫梅琳达·科斯莫,我担心自己可能都认不出她来。我们约好在地方法院对面的咖啡厅见。
我第一次来到利物浦的时候,梅尔<a id="commentRef_17934" href="#comment_17961"><sup>[1]</sup></a>还是个义务社工。现在,她已经是这一带的负责人了(旁人称其为“孩子保护专家”)。很少有人能在社区服务岗位干这么久,因为他们要么做到精疲力竭,要么被烦得勃然大怒。
梅尔的衣着打扮是典型的朋克风格,头发高高竖起,满衣柜都是皮夹克和破破烂烂的工装裤。不管她同不同意别人的观点,她都经常和别人唱反调,因为她喜欢看别人捍卫自己相信的东西。
她在康沃尔郡长大,父亲是当地的渔民,总是用自以为是的口吻教育她,“男人的活”和“女人的活”有什么不同。不出所料,她成了一名偏激的女权主义者,还写了一篇题为《当女人穿裤子的时候》的博士论文。如果她父亲知道这件事,准要从坟墓里跳出来。
梅尔的丈夫博伊德是个来自兰开夏郡的小伙子,经常穿卡其裤和高领毛衣,抽手工卷的雪茄。他高高瘦瘦,十九岁头发就白了,但留了一头长发,扎成一个马尾辫。我只看过一次他披头散发的样子——那是我们打完羽毛球洗澡的时候。
他们很热情好客。我们周末的晚餐派对多数在博伊德家破败失修的阳台上举办,他家有座“风铃”花园,还有一口老旧的鱼池,里面种着大麻类植物。那时,虽然我们工作劳累,不受赏识,却还是很乐观。朱莉安娜弹吉他,梅尔则在一旁唱歌,她的歌声像琼尼·米歇尔。我们会举行素食大餐,一杯接一杯喝酒,再吸点大麻,一起痛批世界的不公,直到周一才能从宿醉中缓过来,胃胀气会一直持续到周三。
梅尔在窗外对着我扮了个鬼脸。她把直发别在脸后,穿着黑色牛仔裤和裁剪合身的米色夹克。她夹克的翻领上方系了条白色丝带,我不记得这是哪个慈善机构的标志了。
“这就是管理人员的打扮吗?”
“不,这是中年女性的打扮。”她笑着说,高兴地坐下,“这双鞋难穿死了。”她说着,把它们蹬到地下,揉着自己的脚踝。
“去购物了?”
“我去了一趟少年法庭,执行紧急护理令。”
“结果还不错吧?”
“没让事情变得更糟就是了。”
我去买咖啡,她负责看着我们的东西。我知道她在观察我——想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改变。她可能在想,我们还有相似之处吗?为什么我突然约她?护理行业的人都格外多疑。
“你的耳朵怎么了?”
“被狗咬了。”
“不要和动物一起工作。”
“我总听别人这么说。”
她注视着我在吃力搅拌咖啡的左手。“你和朱莉安娜还在一起吧?”
“嗯。我们有了孩子,叫查莉。她八岁了。朱莉安娜可能还会怀二胎。”
“她怀不怀二胎,你不确定?”她大笑。
我跟着她一起笑了起来,但随之感到一阵愧疚。
我问起了博伊德。我把他想象成一个老年嬉皮士,和以前一样,穿着亚麻衬衫和旁遮普人的短裤。梅尔转过脸去,但我还是注意到了她眼神里飘过的痛苦神色。
“博伊德去世了。”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继续让沉默蔓延,好让这消息不那么突兀。
“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多以前了。一辆带前保险杠的大货车冲过停车栏,把他撞死了。”
我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她悲伤地笑笑,舔了口勺子里的奶沫。
“人们说,丧偶第一年是最艰难的。我跟你说,感觉就像在暴动中被五十个拿着警棍和防暴护盾的警察抛弃一样。我直到现在也没能接受他去世的事实。我甚至怨过他一阵子。我觉得是他抛下我,自己走了。我故意卖了他的唱片藏品,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傻。结果我又花两倍的价格买回来了。”她嘲笑自己,搅了搅咖啡。
“怎么不和我们说,我们都不知道这回事。”
“博伊德弄丢了你的地址。当时他着急得不行。我其实本来可以找到你的。”她抱歉地对我笑笑,“只是那段时间我谁都不想见。见到你们,只会让我追忆那段美好的旧时光。”
“他葬在哪里?”
“他在家,住在我档案柜的一个小小银罐子里。”她的措辞让人感觉他仿佛还在花园里百无聊赖地散步。“我不想把他埋到地下,太冷了。下雪了怎么办?他不喜欢寒冷的天气。”她悲凄地看着我,“我知道这么做很傻。”
“我不觉得。”
“我想过存钱,把他的骨灰带到尼泊尔。我可以在山顶撒下它们。”
“他恐高。”
“是啊。或许我应该把他的骨灰撒在默西河。”
“你能那么做吗?”
“反正没人能阻止我。”她伤感地笑笑,“所以,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利物浦?你一直不喜欢这里,恨不得赶紧走。”
“真希望你们俩能跟我一起回去。”
“南下?算了吧!你知道博伊德是怎么看伦敦的。他说,住在伦敦的人都在追逐一些别处没有的东西,但那些东西之所以在别处找不到,是因为他们没有费心去观察。”
我能想象出博伊德说这番话时的语气。
“我需要查看一份儿童保护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