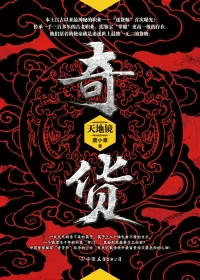烽火戏诸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先前流州那条不知名的廊道,流州步阵对峙阻滞北莽五万南朝边骑!
凉州将军石符确如先前递交拒北城藩王的那道兵文所说,并未率领六千清源军镇精骑火速驰援廊道战场,而是在廊道以南的平原地带站稳脚跟,耐心等待黄宋濮部主力的仓皇北撤,与此同时,需要拦阻南朝边骑援军南下与黄宋濮残部聚拢会合。这位凉州将军仅是象征性派遣一标斥候前往廊道侦察军情。石符停马南望,始终背向那座注定尸体堆积如山的血腥战场,脸色平静,可谓铁石心肠。
最南方的老妪山主战场,凉莽双方以第三次冲锋凿阵最为死伤惨重。寇江淮投入了那支隶属于流州刺史府邸的骑军,黄宋濮也动用了六百余货真价实的重骑军,人马俱甲,每一匹尤为高大健壮的北莽战马都装备有面帘、鸡颈、当胸、身甲和搭后以及寄生,统称铁骑俱装六甲,枪矛难破,弓弩难透。从主将寇江淮手中暂领流州骑军兵权的年轻将领乞伏龙冠,又一次率领仅剩的直撞营骑卒,直奔六百重骑兵。只是在乞伏龙冠一马当先的拼命冲锋途中,徐龙象亲率三百龙象精骑,在战场上逐渐跟上直撞营的铁蹄,最终与直撞营并驾齐驱,一同开阵!
当三次冲锋过后,流州骑军几乎死伤殆尽,龙象军亦是元气大伤。
反观黄宋濮部精锐骑军虽然同样折损惨重,但是数量最多的乙字骑依旧奇迹一般保持极高的完整建制,多达三万骑。按照老妪山战场形势,甚至不需要五万军镇援军赶赴此地,主帅黄宋濮就有十足把握全歼流州野战主力。
但就在此时,一支声势雄壮的骑军,在老妪山东方平原地带闯入视野!那一幕,如日升东海!
这支毫无征兆驰援老妪山的精锐骑军,一字排开,如广陵江一线大潮,由东往西迅猛推进。
这支横空出世的骑军,必然是北凉边军除大雪龙骑之外,最容易被辨认身份的一支边骑,因为每一骑头盔都插有一根雪白雕翎,随风飘摇!每一骑马鞍两侧皆有箭羽透囊而出,如两团胜雪芦花!
铁骑突进,恰如大雪翻涌天地间。
不仅铁甲染血,已经更换两根铁枪,更是满脸鲜血的北莽主帅黄宋濮转头东望,目眦尽裂。
老妪山战场,经过双方皆是不遗余力的三次凶狠凿阵,北莽骑军如今刚好位于最初流州骑军的位置,这原本是这位北莽昔年南朝第一人的算计:在流州野战主力兵力大损,且精气神坠入谷底之际,只要北莽骑军位于南方战场,就能够形成一道阻止流州骑军掉头向南撤回青苍城的天然防线。但事实证明,老帅的算计成功了,可是寇江淮的算计一样达成了,那位年纪轻轻的流州主将根本就没打算撤出老妪山,摆明了是要反过来包夹北莽大军!
黄宋濮没有丝毫犹豫,下令全军竭力向北突围,哪怕北撤途中再遭伏兵阻截,也绝不可恋战纠缠,只管向北!只要与那支应该即将赶至老妪山北方战场的援军碰头,那么胜势仍然在北莽这边!
乞伏龙冠和徐龙象、李陌藩,这三位在老妪山并肩作战厮杀至此的战场将领,根本不用相互招呼,就已经默契地快速变阵,由左中右三军雁字锥阵,变为横向的一字长蛇阵,尽量伸长拉出一条漫长锋线。风水轮流转,开始轮到流州边军以前中后三军冲锋。李陌藩部龙象骑军位于前两排,徐龙象率军居中,乞伏龙冠的残余流州骑军位于最后。他们要做的不再是凿阵杀敌,只需要尽量阻滞黄宋濮部主力骑军突围的马蹄即可!
袁南亭的白羽轻骑,在北莽主力大军的侧翼泼洒出三拨铺天盖地的箭雨后,又有气势如虹的六千骑找准机会,整齐抽刀出鞘,快速冲阵!
如同从北莽骑阵的腰膂处一刀切去,恰好将黄宋濮的嫡系骑军和完颜私骑与三万乙字骑拦腰斩断!
其余主力白羽轻骑开始绕弧向北,并不与北莽大军混战一团,而是凭借负载极轻的轻骑优势,原本由东向西冲锋的骑阵,迅速绕出一个箭头向北的弧线。
若是有人刚刚登顶老妪山俯瞰战场,恐怕都要误认为这支衣甲鲜明的轻骑,是草原骑军的盟友,是在一左一右共同向北而去。
不断有北莽千夫长、百夫长在纷纷绝望之下,率领残部悍不畏死地向右翼白羽轻骑撞杀过去。
只可惜那幅壮烈场景,结局只如石子砸击江水,完全无法打乱白羽轻骑的马蹄步伐。
骑术精湛且体力充沛的白羽轻骑,在遭受一股股北莽骑军的斜向冲锋之后,轻而易举便向右稍稍靠拢,原本大致笔直向前的最左骑阵,出现一处处凹陷,仿佛一只只口袋,任由北莽死士骑卒撞入其中,等待这些草原蛮子的,绝不是近战肉搏的北凉刀,而是娴熟至极的一拨拨骑射。两百骑三百骑的南朝骑军,就这么被割稻谷一般一茬一茬射落马背,没有丝毫撞阵的惨烈,没有死于马背上那种死也死得血肉模糊的死得其所,面对白羽轻骑的精准箭矢,一支支透颅过脖穿胸膛,甚至能够继续策马前冲十数步才跌落马背的北莽骑卒,只有一种死不瞑目的无奈。
老妪山战场最北方地带,只能依稀可见尘土飞扬。
正是宁峨眉麾下四千铁浮屠横插于两座战场之间!
老妪山之巅,寇江淮平淡道:“大局已定,黄宋濮完了。”
陈亮锡同样将战场走势尽收眼底,苍白的脸上浮现一抹笑意,转头嗓音沙哑道:“寇将军当得起‘用兵如神’四字。”
寇江淮望向东方:“怕就怕因小失大。”
陈亮锡疑惑地问道:“老妪山战事结束后,挥师东进增援拒北城,有何不妥?”
寇江淮摇头道:“谁说我们要去拒北城?”
陈亮锡目瞪口呆。
老妪山山脚,李翰林集合白马游弩手,准备再度进入战场。
那名被年轻藩王派遣到此地保护这位白马校尉的秘密扈从武帝城楼荒正要上马跟随,就听李翰林神情坚毅道:“楼荒,你直接去拒北城!堂堂武道大宗师,跟在我屁股后头吃沙子,无趣至极!”
楼荒仿佛一点都不奇怪,坐在马背上,望向那一张张大多年轻的脸庞,最后对李翰林笑着点了点头,打趣道:“小子,可别贪功冒进而死啊,要不然你们那位北凉王可饶不了我。”
李翰林咧嘴一笑:“帮我跟年哥儿说一句,小时候约定的事情,要一起在北莽西京庙堂上撒尿的,他那份,我包了!”
楼荒翻白眼提醒道:“那记得事前多喝水。”
李翰林大笑道:“喝马尿都成!”
楼荒策马离去之前伸出一根大拇指:“我服了!”
廊道之战,六战六却!
北莽南朝边镇骑军整整五万人,已经被逼得彻底陷入疯狂,先后六次冲锋,打得只剩下两万多人!
哪怕明知已经多半无力驰援老妪山战场,哪怕注定要被龙颜震怒的皇帝陛下严厉问罪,这些杀红了眼的草原骑军仍是毫不犹豫地展开第七次攻势。
只要曹嵬率领九千精骑从廊道北口进入战场,再晚上哪怕只有一炷香工夫,烂陀山僧兵和三千流州士卒就要全军覆灭,真正意义上一人不剩!
当曹嵬亲自率领八百死士凿开北莽阵形,一路杀到那座仅剩两百人集结而成的圆形步阵之前后,所见除了尸体还是尸体。
一路而去,碎裂的铁盾、折损的步槊、崩断的陌刀、毁弃的硬弓强弩,四处散乱。
那座所谓的简陋圆阵,不过是人人受伤惨重的烂陀山僧兵和流州青壮,束手待毙而已。
真正抵挡住北莽蛮子骑军冲锋的存在,是一名身披甲胄浑身浴血的修长男子。
武帝城王仙芝大徒弟,中原宗师于新郎!
此人手持一柄斩马陌刀,左右腰间各自悬佩有一柄凉刀,死于他刀下的北莽骑军,已经不下九百骑!
于新郎之前曾经亲口答应过那位年轻藩王,务必保证谢西陲不死!
他不是不可以强行带着谢西陲离开廊道,撤出这座血流成河的战场,但是当谢西陲在亲自浴血奋战、第五次结阵打退北莽骑军之后,对于新郎坚定地摇了摇头。
于新郎一笑置之,并未强人所难,而是从战场上捡回一根长槊和一柄陌刀。
两人并肩作战。
直至谢西陲身受重创,当时这位倒地不起的流州副将被一名负责谢西陲安危的中年僧人从北莽骑卒的马蹄下拽住肩头,然后重重抛向后方,本就精疲力竭处于强弩之末的僧人自己却被数十骑一拥而上,死在当场。
曹嵬部骑军从后方的迅猛杀出,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北莽边骑在勉强抵抗住曹嵬先头骑军的冲杀后,很快就溃不成军。
这些南朝军镇骑卒不可谓不敢战不敢死,否则也不会有七次冲锋赴死,但是曹嵬骑军不合常理地出现,太过突兀,太过凶狠,尤其是在并不宽阔的廊道之中,整整九千骑展开绵延不绝的冲击,好似视野之中,只有北凉铁骑无穷无尽的身影。北莽骑军兵败如山倒,在一名万夫长率领麾下嫡系七百骑对于新郎和那座明明已经摇摇欲坠偏偏不愿倒下的破败圆阵进行最后一轮冲锋后,所有南朝边骑都自主绕过那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陌生武道宗师,快速绕过那座圆阵,果断从两侧向南逃窜。
曹嵬跃下马背,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跌跌撞撞冲入圆阵之内,终于看到那个以刀拄地盘腿而坐的年轻将领,头盔早已不见,铁甲破碎不堪,鲜血模糊了那张原本儒雅的脸庞。
一名只剩独臂的流州青壮,不得不用手肘轻轻抵住这名将领的后背。
曹嵬单膝跪地,颤颤巍巍伸出手掌,轻轻抹去年轻将领脸庞上的鲜血。
年轻将领其实早已失去意识,强撑一口气不愿倒下而已。
于新郎狠狠丢掷出那柄陌刀,将一名纵马南奔的北莽骑军万夫长连人带马劈成两半。
他来到曹嵬和谢西陲身边,蹲下身后,伸手握住谢西陲的手腕:“外伤且不去说,已经伤及内腑,运气足够好,才能有一线生机。”
曹嵬二话不说,转身一拳捶在于新郎胸口,眼眶通红,怒斥道:“徐凤年要你待在谢西陲身边,就只是为了这狗屁‘一线生机’?!”
于新郎没有说话,只是继续低头为谢西陲渡入一股温和气机。
谢西陲不愿走,从未上过战场的于新郎不知为何,也觉得不该走,两人便都不走了。
谢西陲觉得自己应当战死此地,于新郎觉得死在这流州关外黄沙,倒也不算太坏。
只是在多次救下命悬一线的流州副将后,后者怒道:“于新郎!每救我一次,你便会少杀三四人,要我教你这笔账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