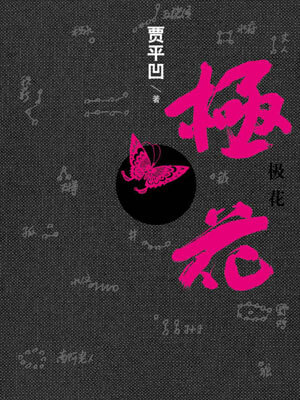柯南·道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但是我并不相信,而他企图把我引开,反而更使我添了几分怀疑。
‘那个女人是朝哪边走的?’
‘我不清楚,先生,我只知道她从这里经过,但是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注视她。不过看起来她似乎步履匆匆。’
‘这有多久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是的,不超过五分钟。’
‘你这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都至关重要,’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这事和我老婆毫无干系,快到这条街的左边去吧。好,你不去我去。’说着,他就向另一边跑去了。
但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拉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里?’我问道。
‘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可是你不要让假线索给迷惑了,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另一侧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些许东西。’
我想,照他的意见办也并无坏处,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看到街上川流不息,人头攒动,来往不绝,每人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所,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然后我们重返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无功而返。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一有脚印便极容易发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可是没发现任何脚印的痕迹。”
“那天晚上雨从未停歇吗?”
“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
“那么,那个女人穿着带泥的靴子,约莫在九点钟左右进入室内,怎能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呢?”
“你能指出这一点,我很高兴。那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在看门人房里有个习惯,那就是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明白了。那么说,即便当晚下着雨,也没有发现脚印,对吗?这一系列事件的确非常有趣。接下来你们又从何着手呢?”
“我们也检查了一遍房间。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里面都插上插销了。地板上铺了地毯,不可能会有地道门的,天花板是用平常白灰刷成的。我敢用性命担保,不管是谁偷了我的文件,只能经房门逃走。”
“壁炉的情况怎样?”
“那里没有壁炉,仅一个火炉而已。电铃线正在我写字台的右边。无论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边去。可是为何罪犯要去按铃呢?这是一个最棘手的疑问。”
“这件事的确非同一般。你们接下来又做什么了?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那位不速之客是否遗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像烟蒂、丢失的手套、发夹或者其他什么小物品?”
“没有发现此类东西。”
“也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我们从未想过这一点。”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素来不吸烟,我想,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我定会闻出来的。但是那里连一点烟味都没有。唯一深信不疑的事实就是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也就是看门人的妻子,就是从那地方匆忙走出来的,看门人也无法解释这个事实,他只是说他妻子往常这个时间都回家了。警察和我都认为,如果文件的确在那个女人手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闻讯立即赶来,全力以赴接过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所述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尚未回来,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
十分钟后,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对此我只能责怪自己。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去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打开门。我们听见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然后我们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穿越过过道。福布斯猛地将门推开,我们两个人跑进作为厨房的后屋,可是那女人抢先走进去了。她敌视着我们,后来,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浮现出尤为诧异的表情。
‘怎么,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为什么躲避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显得十分牵强,’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理由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于是徒劳地提出抗议,并进行徒劳地抵抗。我们叫来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行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是否趁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将文件扔进火里了。但是,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也没有。我们一到苏格兰场,马上把她交付给女搜查员。我十分焦虑,费了好大周折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报告,但是报告说没发现文件。
这时,我才开始对自己的处境有种莫名的恐惧,迄今为止,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及深思熟虑。我一直坚信可以马上找到那份协定,因而我根本不敢设想找不到会有什么后果。可是现在既已茫然无措,我就有闲暇来对自己的处境深思熟虑一番了。这实在很可怕。华生可能已告诉你,我在学校时,是一个怯弱而敏感的孩子。我天性就是这样。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成为这个十分离奇的意外事件的替罪羔羊,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根本不容节外生枝。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可耻地毁了。我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我只是依稀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费尽口舌安慰我。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去沃金的列车。我相信,当时倘若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趟火车同行,那位同事会把我送到家为止。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悉心周到,也确实多亏他如此关照我,因为我在车站就昏倒过一次,在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当我家里人被按铃从睡梦中惊醒,看到我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时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柔肠寸断。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原委,便把经过对我家人悉数说了一遍,但于事无补。谁都很清楚,我的病短时间内是治不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仪的卧室,将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神经极度紊乱,若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照料,以及医生的关照,我就再无与你们讲话的机会了。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护士晚上看护我,因为我神经病发作时,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的头脑渐渐清醒,不过是最近三天的事,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着手于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阐明,想尽一切办法,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以及他的妻子,也未能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于是警方又将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身上,读者应该还记得,戈罗特正是那天晚上下班后在办公室里停留过很长时间的人。实际上,他只有两点可疑之处:一点是他走得很晚,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但是,事实上,直到他走以前,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像你我一样是英国人的。不管怎么说,也找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把他牵扯进去。于是这件案子至此就搁浅下来。福尔摩斯先生,我把最后的期望都托付于你。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
由于谈话过久,倦怠至极,病人便斜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兴奋剂。福尔摩斯头向后仰,双目微闭,坐在那里缄口不语,在一个陌生的人看来,似乎是心力交瘁的样子,不过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非常紧张地思索着。
“你讲得很明白,”他终于说道,“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可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清楚。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
“一个人也没有。”
“比如说,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回沃金。”
“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恰好去探望你吗?”
“没有。”
“你的亲友中有知道怎么去办公室的吗?”
“啊,是的,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
“当然,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那么这些询问就显得多此一举了。”
“我什么也没讲过。”
“你很了解看门人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
“是属哪一团的?”
“啊,我听说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
“谢谢你。我相信,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到些细枝末节。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实,但是他们却不是经常能利用这些事实。啊,多么可爱的玫瑰花啊!”
他走过长沙发,到开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耷拉着的玫瑰花枝,欣赏着娇艳欲滴的花簇。在我看来,这还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因为我以前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物如此热衷。
“天下之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他斜靠着百叶窗,说道,“据此,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建为一门精密严谨的学科。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就是根植于这花丛之中。因为一切其他的东西:我们的本领,我们的夙愿,我们的食物,这一切首先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这种花朵则迥然不同。它的馥郁芳香和娇艳欲滴都是对生命的装饰,而不是生存的条件。只有仁慈才能产生这些不俗的品格。所以我再说一遍,人类在鲜花中寄予了太多的希冀。”
珀西·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在福尔摩斯论证时凝视着他,脸上流露出惊奇和极度失望的表情。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深思之中,这样过了几分钟,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寂。
“你找到了解决这一疑团的希望了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
“啊,这个疑团!”福尔摩斯一愣,才回过神来,回答道,“嗯,倘若否认这件案子复杂而又晦涩,那是愚蠢的。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我要深入调查这件事,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
“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
“你已经向我提供了七个线索,不过我当然必须先验证一番,才能确定它们的价值。”
“你这是在怀疑谁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我的结论下得太快。”
“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精彩绝伦,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我想,华生,我们不能再有更妥当的办法了。费尔普斯先生,你不要抱过高的奢望。这件事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我万分焦灼地等着和你再见面。”这位外交人员大声说道。
“好,虽然不一定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但明天我还是乘这班车来探望你。”
“愿上帝保佑你成功,”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我知道措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就给了我新生的力量。顺便说一下,我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封信。”
“啊!他说了些什么?”
“他显得冷峻,但并不严厉。我断定是由于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责备我。他反复说事关重大,又说只有我恢复了健康,才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否则我的前程——当然是指我被革职——就是海市蜃楼了。”
“啊,这是合情合理而又周全的考虑。”福尔摩斯说道,“走吧,华生,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将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茨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陷入沉思,一直缄默无语,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才张口说话:“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鸟瞰这样一些房子,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不已的事。”
我以为他仅仅是在调侃,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可是他立即解释道:“你看那片矗立于青石之上孤立的大房子,它们,好似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
“那是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朋友!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未来的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定将更加睿智富强。我想,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喝酒吧?”
“我想他不会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