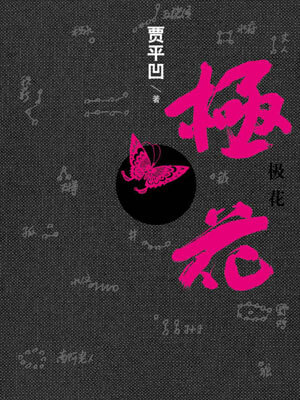斯蒂芬·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才要开口说我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过得怎样时的制式答案,心里就想,我干吗非扯这些“万宝路牛仔”的鬼话不可?我这是要骗谁?眼前这一位,可是在红十字会的护士一替我拔下针头就一定为我奉上巧克力夹心酥的人。我就算跟他明说我不好,又能怎样?引发大地震?大火?洪水?狗屁!
“不太好,”我说,“我最近其实不太好,拉尔夫。”
“流行性感冒吗?现在传染得厉害呢。”
“不是,这一次流行性感冒还真的放过了我。我睡得也还可以。”这倒是真话——“莎拉笑”的噩梦没再回来,不管是正常版还是高八度的尖叫版。“我想就是忧郁了一点吧。”
“嗯,那你应该去度个假才好。”他说完又小啜一口他的咖啡。等再抬眼看我的时候,他皱起了眉头,放下手上的杯子:“怎么了?有事吗?”
没事,我很想跟他说,只是你是第一只打破死寂的鸟儿,拉尔夫,就这样。
“没事,没事。”我说完后,把他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度个假……”因为想感觉一下这几个字从我嘴里讲出来的滋味。
“是啊,”他说时带着笑,“大家都会度假的嘛。”
大家都会度假的嘛。他说的对,就算力有未逮的人,也照样去度假。累的时候,去度假;被麻烦事弄得焦头烂额,去度假;被赚钱、花钱压得喘不过气来,去度假。
我当然有钱度假,也绝对可以暂时放下手边的事——什么事啊?哈哈!——但我却需要由这一位在红十字会发饼干的人,替我指出眼前明摆的出路!亏我还大学毕业!打从我和乔一起去百慕大的那次后,我就再没度过假。那是她死前最后一年冬天的事。磨坊早打烊了,我却还紧盯着磨盘不放。
但要再到夏天,我在《德里新闻》上面看到拉尔夫·罗伯茨的讣闻(被车撞死),我才发现我欠他的有多少。我跟各位说,他的建议比我捐血后喝的橘子汁都要补。
那一天,我离开餐馆后没直接回家,而是跑去轧马路,走遍德里这鬼地方一半的地头,那份只填了一半字谜的报纸夹在腋下。我一直走到身体发冷才停下来,虽然那时气温已经回暖。我什么也没想,却又什么都想。那是很特别的“想”。我每次酝酿文思到了快要可以动笔时,都会这样子“想”。虽然我有好几年没这样子“想”了,但我还是很容易、很自然就会上手,就像我的写作从没断过似的。
我的“想”,就像有几个彪形大汉开来一辆大卡车,把一堆东西搬进你家的地下室——我最多也只能这样解释。你看不出来那些东西是什么,因为全包在棉垫里,但你也不需要去看。就是家具嘛,让家像个家,刚好的家,一切都像你要的家。
等那些彪形大汉爬上他们的卡车走了,你就走进地下室,四下看看(跟我那天早上在德里镇上四处乱走,穿着我的雨鞋上山丘、下溪谷乱走一通一样),摸一摸这边包在棉垫里的弧线,摸一摸那边包在棉垫里的棱角。这一件是沙发吗?那一件是梳妆台吗?无所谓。该有的都在这里,搬家工人什么也没漏掉。虽然得靠你自己往上搬(往往还会害你一身的老骨头腰酸背痛),但没有关系。全都搬来了才重要。
而这一次,我想——或者是希望吧——货运卡车把我往后四十年需要的东西全都送了来。往后这四十年,我可能都得住在“非写作区”。这四十年一股脑挤到了我的地下室门口,礼貌地敲了门,可是连着几个月没人来应门,最后它们只好弄来一具攻门槌来撞门。<b>喂,老兄,这么大声没吓着你吧,不好意思啊,弄坏了你的门。</b>
我不在乎门;我在乎的是家具。有家具坏掉、不见吗?我看没有。我只需要把东西弄上楼,扯掉包在外面的棉垫,放到它们该放的地方就好。
我在回家的途中经过“天幕”。这是德里一家迷人的小电影院,虽然(或者是因为)有录像带革命,但生意还是很好。那个月,他们放映的是五十年代的经典科幻名片。不过,四月时放映的全是亨弗莱·鲍嘉的名片。他是乔一辈子的最爱。我在电影院门口的华盖下面站了好一阵子,端详他们贴的新片海报。等我回到家,马上在电话簿上随便挑了一家旅行社,跟那边的人说我要到拉戈岛。你是说西屿吧,那人跟我说。不对,我跟他说,我是说拉戈岛,鲍嘉和白考尔演的《盖世枭雄》的拉戈岛,我要去三个礼拜。接着又转念一想,我有钱,单身一人,又退休了,这“三个礼拜”是什么意思?加到六个礼拜好了,我说。你帮我找一栋小屋什么的。会很贵哦,他说。我跟他说没关系。等我回德里后,就会是春意正浓的时节了。
在这期间,我有家具要拆。
头一个月,我对拉戈岛很是着迷,可到了最后的两个星期,就无聊得要抓狂了。不过,我还是待了下去,因为无聊也是良方。忍受无聊的耐力高一点,能做的思考也多。我在那里吞了约莫千万只小虾下肚,灌了约莫千百杯玛格丽特下肚,又读了约莫二十三本约翰·麦克唐纳的小说——真要好好算一下的话。我烤焦一层皮,脱掉一层皮,最后终于换得一身古铜色。我买了一顶运动帽,上面用鲜绿色印了“鹦鹉头”几个字。我只在同一片海滩闲晃荡,到后来,每个人我都叫得出来名字。我也帮我的家具拆封。虽然有许多我不喜欢,但每一样都还真的正合我的屋子用。
我想乔,想我们一起走过的人生道路。我想跟她说,没人会把《二即是双》和《天使,望故乡》相提并论。“你别拿怀才不遇那一套屁话来烦我,行不行?努南!”她这样说过……我在拉戈岛那阵子,她这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回响,每一次都是乔的声音:屁话,怀才不遇的屁话,狗屁小男生才会讲怀才不遇的屁话!
我回想乔穿着她那条红木色的长围裙朝我走来,手上的帽子里面满满都是黑色的喇叭菇。她笑得很得意,朝我大喊:“今晚没人吃得比努南家好!”我回想她给她的脚趾甲涂指甲油,上身整个弯下来压在两条大腿中间。女人家要做这件事不用这姿势还真不行。我回想她拿书扔我,因为我笑她剪的新发型。我回想她用她的五弦琴学弹乡村舞曲的神情。她没穿胸罩只套一件薄汗衫的身姿。我回想她哭的模样,笑的模样,生气的模样。我回想她骂我屁话,怀才不遇的屁话。
我也回想我做的那些噩梦,尤其最后一场算是压轴的大噩梦。这很容易,因为那一场噩梦跟别的比较平常的噩梦不一样,并没有因为时过境迁而淡化。我做过的梦中于事过多年之后依然清晰如昨的,就是那最后一场“莎拉笑”的噩梦,还有我生平头一遭的“咸湿梦”(一个女孩子没穿衣服躺在吊床上吃李子)。其他的梦不是糊成一团,就是忘得一干二净。
“莎拉笑”的那些梦,有很多细节我记得很清楚——潜鸟,蟋蟀,晚星,我许的愿望等——但我觉得这些大部分都似真实幻。若真要说的话,只是布景罢了,因此都可以排除在我的考虑之外。这就只剩三个主要的因素,也就是三件最大型的家具需要我来拆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