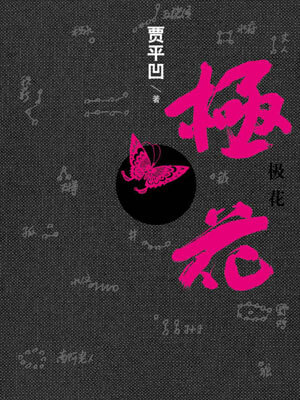雷蒙德·钱德勒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1
四点过后,我离开大陪审团,然后悄悄从后面的楼梯上到方威得的办公室。检察官方威得面容严肃,轮廓分明,留着女人深爱的银白鬓发。他把玩着桌上的笔说:“我想他们相信你了。下午他们可能以杀害沙隆的罪名起诉曼尼·廷南。如果这样,你最好小心些。”
我拿起一根香烟在手指间滚动,最后还是把它放进嘴里。“方威得先生,别派人跟踪我。这个城里的大街小巷,我都很熟,你的人靠得太近,对我没有好处。”
他看着一扇窗户,“你对法兰克·杜尔知道多少?”他问,眼睛却没看我。
“我知道他是个大政客,实权派,如果你要开赌场或妓院——或想要跟市政府做买卖,都得去见他。”
“没错,”方威得严厉地说,把头转向我,然后放低声音道,“抓到廷南的小辫子,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如果除掉廷南,杜尔就有利可图——廷南是他想要拿到合约的那家公司的董事会头头——他会不惜一切代价冒险的。我听说他和廷南有交易。如果我是你,我会对他保持警惕。”
我笑笑。“我只有一个人。杜尔地盘很大,但我尽力而为!”
方威得站起来,隔着桌子伸过手来,说:“我要出城两天,如果起诉成功,今晚就走。小心点——如果有什么差池,找勃尼·欧斯,我的调查组组长。”
我说:“没问题。”
我们握了握手。出门时,经过一个一脸倦容的女孩,她给了我一个疲惫的笑容,看我时,手指卷着颈后的鬈发。回到办公室时,刚刚过四点半。我在小接待室门外停了一下,四处看看。然后打开门,走进去,当然里面没人。
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红色的老式沙发,两张不搭调的椅子,一小块地毯,一张阅读桌,上面摆着几本旧杂志。接待室的门一直开着,让客人能够进来,坐着等候——如果有客人,他们又想要等待的话。
我穿过去,打开我专用办公室的锁,门上写着“菲利普·马洛……专事调查。”
卢·哈格坐在办公桌一边的木椅上,远离窗户。戴明黄色手套的手抓着手杖的手柄,绿色的宽边帽推到了脑袋后半部。帽子下露出非常光滑的黑发,他的头发太长,快要盖住脖子后面了。
“嗨,我等了很久。”他懒懒地微笑着说。
“嗨,卢。你怎么进来的?”
“门一定没锁,或许我的钥匙刚好匹配。你介意吗?”
我绕到桌子后面,坐在转椅上,然后把帽子放在桌上,从烟灰缸上拿起大头烟斗,开始装烟草。
“只要是你就无所谓。我正想要换一个比较好的锁哩!”
他笑了,丰满的红嘴唇绽开。他是个长相非常英俊的小子。他说:“你还在做生意,还是准备下个月蹲在旅馆里和总局的人喝老酒?”
“我还在做生意——如果有人找我的话。”
我点燃烟斗,靠在椅背上,盯着他干净的橄榄色皮肤和笔直乌黑的眉毛。
他把手杖放在桌上,黄手套压在玻璃上,嘴唇蠕动了几下。
“我有个小生意要给你,赚头不大,挣个车费。”
我等着他说下去。
“今晚我在奥林达有个小把戏,就在卡纳利的地盘。”
“白烟的地方?”
“嗯。我想我要走运了——而且我希望有个带家伙的人在旁边。”
我从上层抽屉里拿出一包新的香烟,推过桌面。卢拿起来,打开烟盒。
我说:“什么样的把戏?”
他从烟盒中抽出一根烟的一半,低头盯着它。他的样子让我有点不喜欢。
“我已经休息了一个月,赚的钱不够在这种城市开销。总局那些家伙从禁令后就开始施压。他们一想到要靠薪水过日子,就开始做噩梦。”
“在这里运作的开销不会比其他地方大吧!所有的钱都交给一个组织,就够了。”
卢把香烟塞进嘴里。“没错——法兰克·杜尔,”他嘶吼起来,“那只肥猪!狗娘养的吸血虫!”
我没说话。我已经过了对那些自己拿他没办法的人只能骂骂为乐的年纪。我看着卢拿起桌上的打火机点燃香烟。他喷出一口烟,继续说:“说来好笑,卡纳利买了一个新轮盘——从州长办公室某个吃钱鬼那里买来的,我认识卡纳利的头号庄家手皮纳,很熟。这个轮盘是他们从我这儿拿走的,里面有些猫腻——我知道猫腻在哪儿。”
“但卡纳利不知道……听起来真像卡纳利。”我说。
卢没看我。“他那边生意不错,有个小舞池,一个墨西哥五人乐队,可以帮助客人放松。他们可以先跳几支舞,再回去赌,即使输了,也不会太沮丧。”
我说:“你要干吗?”
“我想你可以把这叫作一套‘运作’。”他轻声说,透过长睫毛看着我。
我移开目光,环顾着房间。房间里铺着铁锈红色的地毯,广告月历下有五个绿色箱,排成一排。角落里有一座老式衣帽架,几张胡桃木椅,纱布窗帘挂在窗前。窗帘尾端因为被风吹来吹去弄脏了。一道黄昏的日光照在我的桌子上,照亮了空气中的灰尘。
“这么说吧!”我说,“你认为你操控了那个轮盘,可以赢很多钱,这会让卡纳利大为光火。你希望一路有人保护——那个人就是我。我觉得这主意烂透了。”
“一点儿都不烂,任何轮盘都有一定的节奏,如果你非常了解它……”
我笑着耸耸肩,“好吧,我不想搞懂这玩意,我对轮盘了解不多。听起来,你好像是想通过诈骗来装满自己的腰包,不过我也可能听错了。反正这也不是重点。”
“那什么才是重点呢?”卢淡淡地问。
“我不是什么好保镖——但这可能也不是重点。我想我应该认为这场赌局是公平的。如果我不这样认为,不肯接受你的工作,结果你进了棺材该怎么办呢?或者如果我认为每件事都在掌控之中,可是卡纳利不吃这一套,发起脾气来呢?”
“所以我才需要带枪的人啊!”卢除了说话,一块肌肉也没动。
我淡然地说:“如果我够凶悍,可以挑起这份差事——我倒是不知道自己很凶悍——那我担心的恐怕仍然不是这点。”
“算了。光是听你说担心,就够我泄气了。”
我又笑了笑,看着他的黄手套在桌面上猛烈地移来移去。我缓缓地说:“你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可以用这个方式赚大钱的人了。当你这么干时,我是最后一个支持你的人。明白了吧!”
卢说:“好吧。”他把烟灰磕在玻璃面上,然后低头吹掉,继续开说,好像在谈论新的话题,“葛林小姐跟我一起去。她红头发,个子很高,迷人得很,以前是模特儿。在任何场合她都是个最佳人选,可以避免卡纳利盯我盯得太紧。所以我们要合伙,我想我应该先告诉你。”
我沉默了一分钟,然后说:“你很清楚我刚刚告诉大陪审团,我看见阿特·沙隆被推出车外,曼尼·廷南伸手出去割掉了他手上的绳子,最后乱枪打死了他。”
卢淡淡对我一笑。“这样一来,那些受贿的就更好过了。拿人钱财,却不消灾。他们说沙隆正派,不让董事会越界,所以被做掉了。”
我摇摇头,不想多谈。我说:“卡纳利很多时候品味奇怪,也许他不喜欢红头发呢!”
卢慢慢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手杖。他盯了会儿一根黄色手指指尖,显出一副困倦的样子。然后他晃着手杖走向门口。
“嗯,我们改天再见了。”他慢条斯理地说。
我等他把手放在门把上才说:“卢,别失望。如果你一定要我陪,我就去奥林达一趟。但我不要钱,还有,看在老彼得的份上,别再吃饱撑的,盯我的梢了。”
他轻轻地舔舔嘴唇,没有正眼看我。“谢了。我会小心为妙。”
他走出去,黄色手套消失在门边。
我静静地坐了五分钟,烟斗变得十分烫手。我把烟斗放下,看看手表,站起来打开桌尾角落里的小收音机。电流嗡嗡声停止后,喇叭传出一声钟响的余音,然后一个声音说:“KLI现在向你报告当地夜间新闻。今天下午稍晚的一则重要新闻是大陪审团终于决定起诉曼尼·廷南。廷南是著名的市政府游说人士,在本市势力庞大。这项起诉令他的许多友人惊讶,起诉依据的证词完全出自——”
电话铃这时尖锐地响起来,一个女孩冰冷的声音在我耳际说:“请等一下,方威得先生要和你说话。”
他立刻接上来。“起诉成立了,小心那家伙。”
我说我刚听到收音机播报。我们谈了一小会儿,他就挂断电话,说必须立刻去赶飞机。
我往后靠在椅子上,听着收音机,但不专心。我想卢真是笨蛋,但这是我没法改变的。
2
星期二有这么多人,生意真好,但没有人跳舞。大约到了十点,五人小乐队玩伦巴玩累了,没有人注意他们的音乐。木琴乐手把棒子丢下,手伸到椅子下拿杯子。其余的人点燃香烟,只管坐在那里,看起来很无聊。
我侧身靠在吧台上,吧台和乐队台都在同一边。我拿着一杯龙舌兰,让杯子在台面上打着转。所有的生意都集中在三座轮盘中间的一座。
酒保在吧台另一边,头凑到我旁边。
“那个火辣的女人一定让他们输得很惨。”他说。
我没看他,点点头。“她现在大把的玩,连算都不算了。”
红发女郎很高。我可以看见她闪着金属光泽的头发,在她背后的人头间异常显眼。我也看见站在旁边的卢油光锃亮的头。每个人好像都站着玩。
“你不玩?”酒保问。
“星期二不玩。我有一次星期二玩,惹了不少麻烦。”
“是吗?你喜欢那玩意不加水?我可以帮你弄得顺口些。”
“用什么顺呢?”我说,“你手边有木锉吗?”
他笑笑。我又喝了一些龙舌兰,然后摆出一脸苦相。
“有人故意发明这玩意的吗?”
“那我可不知道了,先生。”
“那边的最高限额是多少?”
“那我也不知道。我想得看老板的心情。”
轮盘桌排成一列,靠近远处的墙边。镀金的矮栏杆把它们围在里面,客人站在栏杆外。
中间的那桌突然发生了争吵,其他两桌的人纷纷抓起筹码移过来。
然后一个非常清晰、礼貌、带点外国口音的声音清楚而大声地说:“夫人,请您耐心点……卡纳利先生马上就来。”
我走过去,挤到栏杆边。两个靠近我的庄家手把头靠在一起,眼睛朝斜下里望着。其中一个缓缓地在静止的轮盘上来回移动一个耙子,他们都盯着红发女郎看。
她穿着一袭高领的黑色晚礼服,双肩线条优美,皮肤雪白,说不上十分美丽但也称得上漂亮。她靠在轮盘前的桌子边缘。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身前有一大堆钱和筹码。
她的声音单调,好像同样的事情已经说了很多遍。
“快点转这轮子!你们收钱收得很快,就是不喜欢掏出来。”
负责的荷官露出冷冷的木讷的笑容。他很高,黝黑,满脸不在乎的神气。“庄家不能收你的赌注,”他的口气冷静确定,“也许卡纳利先生……”他耸耸平滑的肩膀。
女郎说:“这是你们的钱,小气鬼。你不想要回去吗?”
卢·哈格在她身旁舔舔嘴,一只手放在她的手臂上,两眼热切地盯着那一堆钱。他轻声说:“等卡纳利来……”
“去他的卡纳利!我手气正旺——我要保持好手气。”
这排桌子尾端的门被打开了,走出一个瘦高苍白的男人,直直的黑发毫无光泽,高高的前额皮包骨,扁平的眼睛深不可测。细细的八字胡修成两条几乎成直角的线,撇到嘴角下方正好一英寸处,颇有东方气质。他皮肤很厚,苍白得发亮。
他走到荷官背后,停在中间桌子的一角旁,瞄着红发女郎,两根手指捻着八字胡的尾端。他的指甲带点紫晕。
他忽然微笑起来,又突然板起了脸,好像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笑过似的。他用一种沉闷挖苦的语调说:“晚安,葛林小姐。你一定得让我派人送你回家,我不希望看到钱落入坏人的荷包里。”
红发女郎不太友善地看着他。
“我还不想走——除非你赶我出去。”
“不走?那你想做什么呢?”
“赌这一沓——全部!”
众人的嘈杂声一下子跌入死寂,四下没有一点呢喃低语。卢的脸色慢慢变得死灰一般。
卡纳利面无表情,优雅严肃地举起一只手,从他的晚礼服里掏出一只大皮夹,丢到高个荷官面前。
“一万,”他的声音沉闷、沙哑,“那是我一贯的限度。”
荷官拿起皮夹打开,抽出两沓发声清脆的钞票,拨弄了一下,折起皮夹,沿着桌子边缘传给卡纳利。
卡纳利没有去拿,除了荷官,谁都没有动。
女郎说:“押红色。”
荷官俯身向前,非常谨慎地把她的钱和筹码叠起来,替她把赌注放在红方块上。
他把手放在轮盘的圆弧上。
“如果没有人反对,”卡纳利说,并没有看任何人,“这一局只有我们两个人玩。”
人头攒动,没有人说话。荷官转动轮盘,左手轻轻一抛,把球丢在辙槽上;然后缩回双手,放在大家都可以看见的桌子边缘——当然是放在桌面上。
红发女郎眼睛发亮,嘴巴微微张开。
球在辙槽上跳动,跃过一个明亮的金属方块,滑下轮侧,在号码旁边的叉道上颤动起来。球突然停止滚动,落在双零旁边的红27格里。轮盘停下了。
庄家手拿起耙子,缓缓地把两沓钞票推出去,推到女郎的赌注中,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清出了赌台台面。
卡纳利把皮夹放回胸前的口袋,转身缓缓向门走去,消失在门后。
我松开抓着栏杆的发抖的手指,人们都散开,走向吧台。
3
卢过来时,我正坐在角落里一张小桌旁,吞咽着龙舌兰。小乐队演奏着单调清脆的探戈,一对男女难为情地在舞池上扭着。
卢已经穿上卡其色大衣,领子竖起,里边围着一条白丝巾,脸上带着微妙的熠熠的神情。这回他戴着白色猪皮手套,把一只手放在桌上靠近我。
“两万两千多,”他小声说,“哇,真过瘾!”
我说:“很多钱啊!卢。你开什么车?”
“看到什么不对劲的事了吗?”
“赌局?”我耸耸肩,玩着杯子,“我不擅长轮盘,卢……倒是你的女人有很多不对劲的地方。”
“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卢说,声音有些焦虑。
“好吧!她让卡纳利看起来像个百万富翁。什么车?”
“别克四门轿车,尼罗绿,两盏探照灯,挡泥板有那种翼子板灯。”他的声音依然有些忧虑。
我说:“慢慢开进城,让我有机会跟上。”
他拿走手套,走开了。红发女郎早已不见人影。我看看腕上的手表。再抬起头时,卡纳利站在桌子对面。假八字胡上方的眼睛毫无生气地看着我。
“你不喜欢我这地方。”他说。
“恰好相反。”
“你不到这里来玩。”他是告诉我,不是问我。
“必须来吗?”我冷冷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