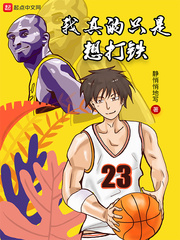弗吉尼亚·伍尔夫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那幅画该清洁一下了。”他说,指着母亲的画像。
“嗨,克罗斯比!”他说。
“这幅画不错,”他又说,仔细打量着画,“不过,那儿草地上不是本来有朵花吗?”
他站在那儿,看着这个在建筑上毫无特色,却无疑居家十分实用的巨大宅子米黄色的门脸,他父亲和姐姐还住在这里。“现在她是越来越会花时间了。”他想,在风中瑟缩着。这时门开了,克罗斯比出现了。
埃莉诺看着画。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好好看过这幅画了。
“老克罗斯比还要让我再等多久?”他站在阿伯康排屋的房子门前,按着门铃,心想。寒风刺骨。
“是吗?”她说。
“西班牙国王的女儿,”他转过街角时哼着,“来看我……”
“是的,一朵蓝色的小花。”马丁说,“我记得小时候……”
这是个肮脏、卑鄙的结局,他想。我过去很喜欢到这儿来。但他讨厌沉迷于令人不快的想法里。有什么用呢?他问自己。
他转过了身。他看到罗丝坐在茶桌边,仍然捏着拳头,他心里涌起了儿时的往事。他看到她背靠教室门口站着,满脸通红,嘴唇闭得紧紧的,和现在一模一样。她本来想让他做些什么。他手里团了一个纸团,朝她扔了过去。
“已经卖了!”马丁说。他稍稍绕了点路,来看看布朗恩街的房子。而房子已经卖了。这红色的字条让他很震惊。已经卖了,而迪格比才死了三个月——尤金妮也不过一年多一点。他站了一会儿,注视着满是尘土的黑窗户。这房子很有特色,是十八世纪建造的。尤金妮对这房子非常自豪。我过去很喜欢到这儿来,他想。可如今,门口地上扔着旧报纸,栏杆上缠着乱七八糟的稻草;因为没有窗帘,他能透过窗户看到里面的空房间。地下室里有一个女人正从一个笼子的栏杆后面抬头看他。再按铃也没用了。他转身离开。他走上街道时,心里感到有什么东西熄灭了。
“孩子们的生活多么糟糕!”他穿过房间,朝她挥着手说,“不是吗,罗丝?”
房屋中介的告示板上贴了一长条鲜红色的纸,上面写着“已售”。
“是的,”罗丝说,“而且他们没人可说。”她又说。
马丁站在那儿。
又是一阵狂风,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门铃响了。就等他按铃吧,按吧,她吼道。她再也不会去开门了。他就在那儿,站在门口。她可以看到栏杆旁立着的一双腿。任他想按多久就按多久。这房子已经卖出去了。他难道看不见告示板上写的通知吗?他不会读吗?他没长眼吗?她朝着火炉缩得更紧了,火上已经裹住了灰白的炭灰。她能看到他的腿在那儿,站在门口,在金丝雀笼子和那堆脏衣服之间,她本打算去洗的,可这风吹得她的肩膀疼得受不了。让他把房子都按垮吧,她才不在乎呢。
“皮姆小姐的温室吗?”马丁手放在门把上,停下了。
看房人马蒂·斯泰尔斯,在布朗恩街的房子地下室里缩成一团,她抬起头看着。人行道上一团尘土被吹得哒哒乱飞。尘土从门缝、窗框缝飘进了屋,飘上了柜子和梳妆台。但她并不在意。她是一个不幸的人。她本以为这份工作很安稳,至少能做到夏末。结果夫人去世了,先生也一样。她是通过她儿子得到这份工作的,她儿子是个警察。这房子及地下室在圣诞节之前是不能租出去的——他们是这么告诉她的。那些由中介安排来看房的人,她只需带他们四处看看。她总是提到地下室里有多么潮湿。“看天花板上的水渍。”确实有,没撒谎。也都一样,从中国来的那帮人照样喜欢。他说,这房子很合适。他在城里做生意。她是个倒霉的人——过了三个月得到了证明,她只好寄宿到皮姆利科她儿子的家里。
“皮姆小姐?”埃莉诺说,“她已经死了有二十年了!”
正值三月,吹着风。其实不是“吹”,而是刮,是鞭打。如此无情的风,如此不合时宜。它不只是吹白了脸庞,在鼻子上吹出了红点;它掀起裙子,露出粗壮的腿,把长裤吹得紧贴腿上,显出瘦骨嶙峋的小腿。这风里没有圆滚滚的果实,反而更像一把长柄大镰刀弯曲的刀刃,割起来十分锋利,只是割的不是玉米;它摧毁一切,为这不毛之地狂喜。一阵狂风它吹走了颜色,即便是国家美术馆的伦勃朗画作,或是邦德街橱窗里的纯色红宝石,一吹就没了颜色。若说它有哪个繁育之地,那就是道格斯岛上,在某个被污染的城市的河岸边,毫无生气的济贫院旁摆满的马口铁罐子里。它将腐叶抛起,令它们的存在状态更加低级,鄙视它们、嘲弄它们,却没有别的东西来代替这被鄙视、被嘲弄的一群。腐叶坠落。风呼啸而过,呼啸着它摧毁一切的喜悦,它的能量——剥去树皮、吹落鲜花、露出白骨。它一成不变、枯燥无味地吹白了每一扇窗户,将老先生们吹进了俱乐部里弥漫皮革气味的越来越深的深深处,将老夫人们吹到卧室和厨房里,两眼无神、面颊僵硬、无精打采地坐在流苏装饰的椅套上。它肆意放纵,吹空了街道,扫清眼前的活物,猛地吹至海陆军商店外停住的一辆垃圾车,吹落在人行道上,散落的一堆旧信封,一卷卷碎发,各种废纸,血迹斑斑的、黄渍斑斑的、染污了油墨的,将它们吹得刮过地面,刮上石膏雕像的腿、灯柱、邮筒,狂乱地紧贴住路边的栏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