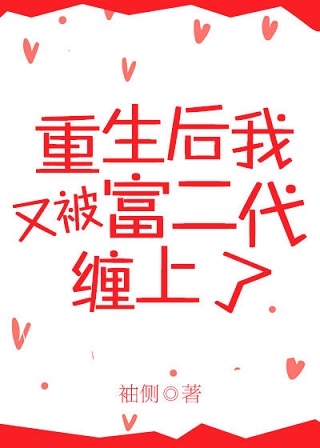约翰·康奈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们握了握手,伍里奇站了起来,抖去衬衫上的煎饼屑。“到处都是。”他说,“等我死掉的时候,估计人们还能从我的屁股缝里找到煎饼屑。”
伍里奇和我没有去往拉斐特。我们离开高速公路,驶上一条双车道,在沼泽中穿行了一段时间。随后,车道变成了被车辙压出的小路,路上有许多小水坑,沼泽的水臭气熏天,许多昆虫伴着热气嗡嗡乱叫。柏树和柳树沿路生长,其间还有一些光秃秃的树桩倒映在沼泽中,似乎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砍伐。睡莲的花瓣簇拥在岸边。放慢车速后,在特定的光线下,我能看到许多鲈鱼在暗影中懒洋洋地游动,偶尔跃出水面。
<aside id="footnote-8-27" type="footnote">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1593—1633),英国玄学派诗人。
“我把它称为玄学领带,”伍里奇说道,“也叫乔治·赫伯特<sup><a href="#footnote-8-27" type="noteref"> </a></sup>领带。”
<aside id="footnote-8-9" type="footnote">让·拉斐特(Jean Lafitte,约1780—约1823),19世纪初期活跃在墨西哥湾的法国海盗、私掠者,曾在1815年新奥尔良战役中协助美军抵抗英军。
我曾听说让·拉斐特<sup><a href="#footnote-8-9" type="noteref"> </a></sup>的海盗们住在这里。现在,有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杀手和走私犯利用运河及沼泽藏匿违禁品。这里也是被害者幽深的绿色坟墓,他们的尸体成为大自然的肥料,植物的气味掩盖了他们的尸体腐烂时发出的恶臭。
“我喜欢你的领带。”我说。它是亮红色的,上面装饰着羔羊和天使。
我们又转了个弯,此时路边只剩下柏树。我们经过一架木桥,它的油漆已经剥落,现出了原本的颜色。在木桥尽头的暗影中,我看到一个高大的人正望着我们,树荫下很暗,衬得他的双眼像鸡蛋一样白。
相比我们上次见面,他长胖了一些。由于衬衫被汗浸湿了,我能看见他的胸毛。一缕缕汗水从他日益灰白的头发间滑落下来,顺着颈部的赘肉流淌。对他这样身材高大的人来说,路易斯安那州的夏天一定非常难熬。伍里奇看起来就像一个小丑,有时还会做出一些滑稽的举动,但是在新奥尔良,任何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不容小觑。那些从前瞧不起他的人已经在安哥拉监狱中腐烂了。
“看见他了吗?”伍里奇问。
他离婚了,这段不欢而散的婚姻大概持续了十二年。他的妻子改回了原名凯伦·斯托特,近来和一位室内设计师结婚,两人一起生活在迈阿密。伍里奇唯一的女儿丽莎也在母亲的坚持下改姓斯托特,他说她在墨西哥加入了某个组织。丽莎只有十八岁。她的母亲和继父根本不管她。伍里奇很在乎她,但是也无法为她做什么。我知道,家庭的不幸令他尤为痛苦。他自己也成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他的白人母亲很糟糕,父亲虽然善良,但没有话语权,无法管好自己的妻子。我认为伍里奇本想当个好父亲。我相信在苏珊和詹妮弗死去时,他比别人更能理解我的难过。
“他是谁?”
伍里奇是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的助理特工主管,他的办公地点是普瓦德拉街1250号。他是为数不多偶尔和我保持联系的前警察时代联系人,也是仅有的几位能不让我气得诅咒联邦调查局的创始人胡佛的联邦探员。另外,他也是我的朋友。谋杀案发生后的那些天,他一直支持我,从不问我什么,也从不怀疑我。我还记得他站在墓地中,全身都被淋湿,水从他那顶超大的软呢帽边缘滴下来。很快,他就被调到了新奥尔良,这说明他在另外至少三个办事处的学徒期都很成功,而且在曼哈顿城区的纽约办事处那混乱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
“老婆婆的小儿子,蒂·吉恩。她管他叫小吉恩。他的智力有些问题,但也会照顾她。他们都会照顾她。”
他穿着一套便宜的棕褐色西装,丝绸领带抻得很长,有些褪色。他懒得系好衬衫领口的纽扣,宁愿让领带落魄地耷拉着。他脚下的地板上撒满了白糖,他坐的那把绿色的树脂椅子空出来的地方也都是糖屑。
“还有谁?”
伍里奇坐在世界咖啡馆靠里侧的一张桌子后面,旁边是一台泡泡糖机,他的背靠在墙上。桌上有一杯热气腾腾的欧蕾咖啡,还有一盘点缀着糖屑的热煎饼。窗外,人们从迪凯特匆匆赶来,经过绿白相间的咖啡馆篷顶,前往大教堂或杰克逊广场。
“家里有六个人。老婆婆,她的小儿子,二儿子的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女儿。她的二儿子死了,三年前和妻子一起死于车祸。她还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住得离这里不远。当地的村民也会照顾她。她大概是这里的女族长吧,也是地位最高的人。”
于是,沃尔特的问题将我带回了4月末的新奥尔良。当时她们已经死去了将近四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