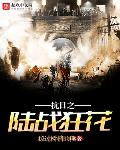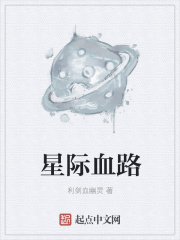第六章 数字韧性
孙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引用了马克·布洛赫《法国农民史》里面的两句话:“由于难逃失败和最终被屠戮的命运,大规模起义一般被迅速瓦解而不会取得任何持久的成效。然而,农村社区中经年累月的坚韧的、沉默的顽强抗争将比大规模起义的昙花一现更为有效。”在斯科特的笔下,马来西亚的农民通过拖沓行动、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痴卖傻、诽谤话语、纵火破坏等进行自卫式的消耗战,这种低姿态和心照不宣的反抗方式避免了公开反抗的集体性风险。斯坦丁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认为朝不保夕者完全无法掌控劳动或工作,这种观点也有局限性。因为在努力程度、配合程度以及技能的应用方面,总是存在暧昧不明、暗中角力的空间,而蓄意破坏、顺手牵羊和磨洋工等行为也并不鲜见。”对于大多数骑手来说,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他们作为“弱者的反抗”也无处不在。概括来说,骑手的反抗策略包括两种:一种来自劳动日常,另外一种表现为公开挑战。前一种多是沉默的、悄无声息的,后一种是具有煽动性的,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在下面的小节中我会呈现,在互联网急速发展的当下,骑手如何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发声。正如斯科特所说,“反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存的劳动控制形式和人们所相信的报复的可能性与严重程度”。平台劳动的强组织性和弱契约化使外卖劳动变成了一种原子的、个体化的自主劳动,这促使作为“弱者”的骑手诉诸更具联结性、集聚效应的媒体技术来进行抗衡。
在国内语境下,相较于单纯地讨论外卖骑手大规模集体行动的可能,一个更有效的视野可能是看到围绕数字劳动框架本身,外卖员群体所形成的主体性、能动性。这里的主体性既包含社会生产,也涵盖社会再生产。“数字韧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不再将描述的范围限定在罢工、抗议这样的直接对抗与冲突中,而是囊括了更广泛的能够彰显数字劳动者个体的、主体性的实践与活动。因为无论是在组织模式还是用工模式上,平台劳动与传统的制造业劳动都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差异也投射到骑手的反抗层面,越来越多细致入微的技术性反抗、媒体反抗正在形成。如果从数量上讲,这样的体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它极有可能产生持久且深远的影响。因此,我想跳出西方福利社会以来所形成的“控制-反抗”框架,回归本土语境。本章讨论的“数字韧性”是一个涵盖了外卖员工作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动态框架,它关注能动性发挥的日常氛围和具体情境,也关注数字技术和流动性给这个群体带来的能动性涌现的新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所讲述的“数字韧性”与欧美语境中具有自上而下的政策、组织和社会救助的韧性社区存在明显差异。这里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外卖骑手的数字韧性具有强烈的日常感。换句话说,它并不是有意为之、刻意形成的,而是嵌在劳动者日常的送单、等单劳作之中,像欧美社会所关注的诸多结构性指标如协商制度、谈判机制、薪资水平等,并不在此次分析框架之内。其次,这里的数字韧性带有鲜明的流动语境。从工作节奏与个人的生命历程出发,跑外卖是一项充满不确定和高流动的工作。外卖经济下的流动被精准地预设、组织和管理。这样的流动性管理不仅仅是算法和技术在起作用,还包括多层级、错综复杂的线下管理体系和人际关系。因此,外卖员所呈现的数字韧性包含了在高度流动性下的决策、应对和自我管理,与静态的社区管理并不相同。
以在地化零工劳动为特征的平台服务业中,矛盾与冲突并不少见。2018年至2024年,多个省份爆发平台服务行业的抗议或罢工,其中,骑手群体的反抗和罢工并不少见。虽然外卖平台下劳动者的抗争可见性日益增强,但是他们的组织性和凝聚力相较于传统产业工人有着明显减弱。这当然与两者不同的组织管理、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将会在下面的章节说明,外卖员群体会出现诸如之前学者所描述的集体抗争行动,但是具有显著社会影响力或取得明显成效的集体行动并不多。围绕平台资本所展开的既庞大又精细的数字化生产模式,使外卖骑手的个人化、个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其联合性大打折扣,即便有抗争的韧性和能动性,也是一种“依附能动性”(contingent agency),即在无法产生重大变化的协商下展开小规模的、情境化的反抗行动。
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可能很难将骑手归为一个职业社团,毕竟它是一个新兴职业,其未来的发展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但骑手正在形成一个劳动社群,这无可争议。其诸多言语、表达、交流方式正在因为媒介技术的应用而日益完善和稳固下来,形成属于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和社群实践方式。埃蒂纳·温格(Etienne Wenger)曾提出“实践社群”(communities of practices)的概念,认为人们的认知大多来自一套“社会学习系统”(social learning system),而这套系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实践社群”的存在。自人类存在伊始,社群便已存在。“实践社群”的出现得益于三个层面的因素:参与者共同发展社群、彼此支持、形成社区资源。对于外卖骑手来说,他们的话语和行为越来越倾向于组成自己的“实践社群”,而且这样的社群正在经历非常明显的数字化——借助数字社群展开劳动生活和抗争成为新一代零工人群的重要特征。本章将从三个具体语境出发来展现骑手的数字韧性,第一节讲述的是一群特殊骑手的故事,即家属患有白血病的骑手如何利用过渡性来争取自我和家庭的生存空间;第二节关注骑手“逆算法”的劳动实践策略,即骑手面对算法如何发挥能动性与其斗智斗勇;第三节关注骑手的媒介使用与以此形成的抗争政治。
本章旨在阐释外卖骑手如何展现自我的数字韧性。“韧性”(resilience)这个概念来自于拉丁文的 resilo,含有适应、回弹的意思。随着词语的广泛使用,这一概念也具有了跨学科意涵,在不同的学科里所指不同。如在环境学和生态学中,“韧性”指的是人或者物在干扰性事件中的适应力;在社会学中,它指的是一个社群在遭遇干扰和破坏时的适应与恢复能力。近些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引发了人员流动的阻滞,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社区管理、数字连接等层面的诸多思考。学者加德尔·乌德万(Ghadeer Udwan)、科恩·勒斯(Koen Leurs)和阿曼达·帕斯·阿伦卡尔(Amanda Paz Aléncar)在对荷兰移民的数字化进行研究时发现,移民群体能有效使用信息传播技术来组建基于社群的数字健康、数字支持和数字认同,他们将这种由数字技术所形塑的能动性统称为“数字韧性”。同样,外卖员也会在劳动实践中发展出符合自身劳动特点的数字韧性。这里的数字韧性指的是骑手在全面数字化的劳动和生活环境中所展现出来的技术能动性,它包括很多内容,如对现有媒介的娴熟使用,通过数字技术重新编排自己的生活,拓展线上空间的社交关系,形塑组织化力量与社群团结,通过“逆向工程”反抗算法监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