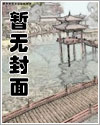沈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
《忆语》对小宛之死,确未作详尽的记载,而对治学、品茗之类,却琐琐写来,不厌其详。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便是他早已写过两千多字的哀辞。《忆语》开头时,有自述其写作动机云:“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格于声韵不尽悉,复约略纪其概。每冥痛思姬之一生,与姬偕九年光景,一齐涌心塞眼。”这是说,小宛死后,他先作了数千言的哀辞,因限于韵文,不能详记,故又作《忆语》。余怀《板桥杂记》也说:“辟疆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哀辞)哭之。”既然已经有一篇哀辞,《忆语》就不再耗费笔墨了,所以就把董小宛之死做弱化处理,而宕开笔墨去记述董小宛生前种种形状。如果还有其他原因,恐怕就是董小宛之死让冒襄不胜凄哀,不忍心再去回忆如此生离死别的惨状,所以就语焉不详了。
<a id="ch1" href="#ch1-back">(1)</a> 家难剧起:指乙酉年十二月如皋遗民暴乱。
由于《忆语》中对小宛在冒家时的一言一行,都写得很周到,但对她的死亡却语焉不详,所以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由于文章末尾写到冒襄移居“友云轩”,夜半三更梦见还家,举室皆见,独不见董小宛,焦急地询问妻子董小宛何在,妻子不答,还背着自己黯然下泪,似乎有难言之隐。于是冒襄梦中大呼曰:“岂死耶?”一恸而醒。而回来之后,董小宛也说做了一个不祥之梦,梦见自己被强人掠走。因此有人推断董小宛是被掳入宫为清世祖顺治宠妃。这显然有些牵强附会,因为董小宛比顺治大十四岁,此时的顺治还是一个小小少年。
<a id="ch2" href="#ch2-back">(2)</a> 披拂,指扇风。
冒襄和董小宛的爱情也许并不是完美的,但确是真实的。没有“一见钟情”的开头,也没有“白头到老”的结局,但是他们九年的夫妻生活却不乏“琴瑟和谐”和“诗情画意”的片断。冒襄汇编评注《全唐诗》,董小宛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两人经常一起伏案工作,“稽查抄写,细心商订,永日终夜,相对忘言”。不仅如此,她在编书过程中还专门收集有关古今妇女生活的种种记录,编成了“瑰异精秘”的《奁艳》一书。他们还一起品茶谈诗,“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沉香泛,真如木兰沾露,瑶草临波,备极卢陆之致”;一起“静坐香阁,细品名香”。难怪冒襄回忆起他和董小宛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会发出如此感叹:“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
<a id="ch3" href="#ch3-back">(3)</a> 鹿鹿:同“碌碌”,即漫漫长夜。
文章并没有到此戛然而止,也没有落入另一个俗套,结婚以后并不意味着从此男女主人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从冒襄的回忆自述,虽然董小宛的婚后生活表面上看来是夫妻琴瑟和谐,全家“咸称其意”,但是其中的辛苦与冷暖只有董小宛自己知道。作为一位出生风尘的女子,进入宦族之门,如果不能俯首低眉,取悦上下,那地位自然岌岌可危。所以她只能“却管弦、洗铅华”,一扫曲院中人的生活习惯,服劳承旨、亲操杵臼,谦恭慈让,一心学习传统的“妇德”。读到“当大寒署,折胶铄金时,必拱立座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这些片断,我们就不难想象她在冒府过的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的日子。待到清兵南下,她跟随冒襄一家辗转逃难,历经艰辛。在最危险的时候却成了最先被抛弃的对象,这也不能全怪冒襄的薄情,应该说这时的冒襄已经对董小宛有了很深的感情,只是在当时封建礼法森严的社会,父母大于妻子儿女,而妾比妻子儿女的地位更低,所以自然是会被最先抛弃的。董小宛也心甘情愿地说:“当大难时,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儿子、幼弟为是。彼即颠连不及,死深箐中无憾也。”最后还是冒襄的父母念及董小宛往日的恩情,使她避免了被舍弃的命运。最感人的还是她在冒襄病重的时候,衣不解带,日夜服伺,几次把冒襄从死神手中夺回。文章写到“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边,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伸起伏,为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适,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与吁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当大火铄金时,不挥汗,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凡我意之所及与意之所未及,咸先后之”……她如此尽心尽力,不但深深感动了自己的丈夫,也使我们读者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