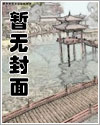易中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马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41年。起因,仍然是魏国攻打别人,齐国去救。打谁呢?说不清。光是司马迁,就提供了好几种说法。《魏世家》说,魏国攻打的是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援。《田敬仲完世家》也说,魏国攻打的是赵国,但向齐国求援的是韩国,因为韩国跟赵国是哥们。《孙子吴起列传》则说,魏国攻打的是韩国,而且是联合赵国一起去打,赵国又变成了魏国的同伙。反正这回,齐国又出来插一杠子,又坏了魏国的好事。于是魏惠王大怒,任命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领,率领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杀向齐国。
这意思是说,善于作战的,总是能够调动敌人,却不被敌人调动。能让敌人自己来,靠的是利诱;能让敌人不敢来,靠的是威胁。其实,能让敌人不得不来,也靠威胁。庞涓攻克邯郸以后,人困马乏,齐军趁机向大梁发起进攻,庞涓也不得不回师救国。孙膑算定魏军必经桂陵(在今河南省长垣或长葛),就在桂陵设下埋伏,狠狠地教训了庞涓一顿。这就是桂陵之战。孙膑这一招,当然不是“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但如果“活学活用”,大约也可以杜撰一句话,算作“能使敌人不得不至者,害之也”。至于“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马上就会讲到,因为它就体现在马陵之战。
齐国这边,派出的将领仍然是田忌,军师也仍然是孙膑。他们率领的“维和部队”,当时已经到了外黄(今河南省民权县)。这时,孙膑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孙膑说,魏国的军队,一贯瞧不起我们齐国,认为我们齐国人都是胆小怕事的。我们这次,也一定要给他这样一个印象。怎么做?第一,撤退,从外黄往马陵撤。马陵在哪里?说法不一。较多的学者,主张就是原来属于山东、现在属于河南的范县。第二,减灶。具体地说,就是埋灶做饭的时候,第一天挖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挖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挖三万人吃饭的灶。这样一来,给庞涓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齐国的军队不到三天,就跑一半了。这就是《孙子兵法·始计》所谓“能而示之不能”(明明能,但告诉敌人不能),也就是忽悠。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
庞涓果然上当受骗。他得意洋洋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国人是胆小鬼!于是,庞涓舍弃了他的步兵,带着精锐部队,日夜兼程,一路狂追。孙膑呢,也算准了庞涓赶到马陵,必定是晚上。马陵道路狭窄,地势险要,正是打埋伏的好地方。孙膑就如此这般地做了一系列安排,然后稳操胜券地以逸待劳,单等庞涓来送死。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后来还成为“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可惜,这只是一个故事。史实可能是,齐军并没有直奔大梁,而是在半路攻打平陵(今山东省定陶县)。魏军也没有回师,而是全力攻城,并拿下邯郸。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拿它来说事,因为“围魏救赵”的主意,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孙子兵法·虚实》说——
当晚,庞涓的部队如期追了过来。这个时候,他一门心思只想生吞活剥了孙膑,心切呀!赶过来以后,天已经黑了。但见黑黝黝一片树林,只有一棵树上有一片白。庞涓就下令钻木取火,点起火把来,看看咋回事。结果,魏军举着火把来到树前,发现这棵树被削了皮,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明白,自己中计了,但也来不及了。魏军一行字没读完,齐军已是万箭齐发。原来,孙膑早将一万弓箭手埋伏在周围,而且下达了“看见火光就射箭”的命令。魏军的火把,等于是发信号。自知大势已去的庞涓只好自杀,魏国的那位太子也做了俘虏。这就是马陵之战。
机会说来就来。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率领甲士八万人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情急之下,赵国向齐国求援。于是,齐威王就任命田忌做统帅,孙膑做军师,发兵救赵。孙膑因为是腿断了的,就坐在车子里面,外面蒙上帷帐,跟着田忌出去打仗,给田忌出主意。田忌就问孙膑,我们怎样救赵国呢?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既然赵国的国都邯郸被围了,那就应该直奔邯郸。然而孙膑的主意却是奔大梁,进攻魏国的国都。因为庞涓作为魏国的将领,当他自己的国都被人家攻击的时候,是不能不回来救的。要救,就得撤兵。庞涓撤兵,邯郸也就解围。反倒是他自己,匆匆忙忙往回赶,功亏一篑不说,还劳民伤财。这就既解救了赵国,又让魏国损失惨重,确实一箭双雕。
现在看来,庞涓这个人,兵法真是没学好。《孙子兵法·兵势》说得很清楚——
孙膑呢?倒是藏起来了。他先是藏在了齐国使者的车子里,后来又藏进了齐将田忌的府邸中。而且,由于田忌的推荐,孙膑还成为齐威王的座上宾。这就注定了孙膑与庞涓,迟早会有一战。设计陷害孙膑的庞涓,也注定要受惩罚。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庞涓到了魏惠王那里,很受重用。但他有一块心病,就是知道自己的能力,比不上孙膑。于是,庞涓就做了一件缺德事。他把孙膑同学悄悄叫到魏国,然后栽赃,害他受了膑刑和黥刑。膑,就是剔掉膝盖骨;黥,就是在脸上刺字。孙膑受了膑刑,所以叫“膑”。庞涓认为,一个脸上有字、站不起来的刑徒,是不可能当什么三军统帅的。天底下最牛的军事家,那就只可能是自己了。至于孙膑,庞涓为他设计的前途,是藏起来,没脸见人。
也就是说,善于调动敌人的,让他往哪他往哪,给他什么他拿什么。用小便宜引诱他,用大部队等待他。这几条,孙膑都做到了,庞涓也都照办了。孙膑要他去马陵,他就“从之”;要他占便宜,他就“取之”。要他中埋伏,他就钻进去。很“配合”嘛!
孙膑是孙武的后代,与庞涓原本是同学。后来,庞涓到了魏国,当了魏惠王的将军。魏惠王,就是《孟子》一再提到的梁惠王。他是魏国的国君,因为把国都迁到了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所以又叫梁惠王。魏惠王的祖父是魏文侯,父亲是魏武侯。他自己继位以后,二十多年间做到最强,是战国群雄中第一个称王的(楚人称王是在春秋)。
这就是“让敌人犯错误”的三招:威胁、利诱、忽悠。说到底,就是“兵以诈立”(《军争篇》)。孙子为什么要说这话?因为在他的时代,春秋早期、中期那种温文尔雅、行礼如仪、费厄泼赖的战争,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尔虞我诈、杀人放火、无所不用其极。这就不能再“温良恭俭让”,不能再把战争当“奥运会”开了。实际上,《孙子兵法》一开始,也就是在《始计篇》,就说得非常明确——
有战例吗?有。这里可以讲两个,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为什么讲这两个?因为都是孙膑指挥的。对手,也都是魏国将领庞涓。这两次战争,《史记》《战国策》《竹书纪年》《孙膑兵法》都有记载,但某些地方有出入。咱们也就别太较真,权当故事听吧!
兵者,诡道也。
所以,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两面三刀”。两面,就是利和害;三刀,就是威胁、利诱、忽悠。威胁,就是让他们“因危而战”;利诱,就是让他们“因利而动”;忽悠,就是让他们“以为有得”。这三刀,都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原则的反用。
这是对的。战争,不是慈善事业,也不是“学雷锋”,没那么多道德诚信可言。要讲道德诚信,只有不要战争。或者说,只有在和平环境中和法治前提下的公平竞争,才能讲道德和诚信,也应该讲道德和诚信。战场上,就讲不得这个。相反,还要把威胁、利诱、忽悠那一套,玩得不动声色、得心应手、炉火纯青。
立于不败之地,只能“保本”。要想获取“红利”,还得让敌人犯错误。如何让敌人犯错误呢?说白了也只有两个字——利害。前面说过,战争,归根结底是利益的驱动。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就更是如此。因此,在战争中,就不能不考虑成本和效益。或者说,考虑获取和损失。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血本无归,固然不对。杀敌三千,自损八百,也不合算。因此,孙子告诫后人,战争的经济学原则,就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篇》)。这条原则,可以用于自己,也可以用于敌人。怎么用?帮敌人打算盘。或者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或者让他们觉得危在旦夕,他们就一定会跟着我们的指挥棒走。当然,帮敌人打算盘,所有的数据,都得是假的,或者真真假假、半真半假。
怎么玩?我想起了一个人。谁?老子。此公,恐怕也是精于此道的。是不是呢?看完下一章,诸位自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