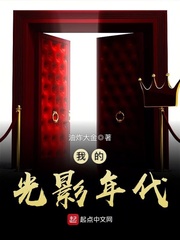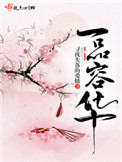易中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当然,韩非也讲“无为”。但他讲的“无为”,是“君无为,臣有为;人无为,法有为”。君为什么要“无为”?因为“明君无为于上”,则“群臣竦惧乎下”(《韩非子·主道》)。君主无为,是为了让臣子害怕。何况,君主不做事,不等于别人不做。谁做?天下臣工。这叫“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臣工做事,也不是乱做,得依照制度。这就叫“以法治国,举措而已”(《韩非子·有度》)。君主自己,则阴一手,阳一手。法制写在脸上,权术藏在心里。一只袖子里藏大棒,另一只袖子里藏胡萝卜。这,就是“帝王术”了,跟庄子的“逍遥游”完全两码事。
奥秘之一,恐怕就在“无为”。也就是说,老、庄、韩,都讲“无为”。但庄子是“真无为”,韩非是“假无为”。庄子这一生,宁愿住在穷街陋巷,缺衣少食,不知“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也不肯出来做官。别人请他,他还要讽刺别人。他理想的生活,是在一棵硕大的树下睡懒觉,或者在江河湖海自由自在地漂。别人是管他叫牛还是叫马,也不在乎。韩非则不同。他要做谋士,为君主谋,还要设计国家制度。谋不成,就写书,告诉君主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以说是“既出谋画策,又保驾护航”。韩非,岂能“无为”?
问题是,这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这里有问题。什么问题?第一,《周易》在《老子》之前,有区别,不奇怪。孔子是老子的批判对象,不相同,也不奇怪。韩非却是推崇老子的。他甚至可以说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人之一,怎么差别也这么大?第二,老子思想的继承人,有两个,一个是庄子,一个是韩非。然而韩非与庄子,却天差地别。我在《先秦诸子》一书中讲过,庄子与韩非,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庄子认为人性本真,韩非认为人性本恶。所以,庄子追求绝对的自由,韩非主张绝对的专制。庄子希望的,是社会的宽容;韩非强调的,则是国家的管制。如此南辕北辙,怎么都是老子的“学生”呢?
关系就在于,老子的无为,也可能是假无为。
老子就不这么讲。老子的说法,前面也讲过,是“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是是是,滚滚滚,有区别吗?没区别。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有区别吗?也没有。为什么?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它们都是会变的嘛!这就要讲转化,不能讲斗争。可见,韩非的矛盾论,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而且“你压倒我,我压倒你”。老子的辩证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你变成我,我变成你”。所以,韩非是斗争的哲学,老子是转化的哲学。这是老与韩的区别。
有这个问题吗?有。因为有一句话,我们弄不清老子是怎么说的。什么话?无为而无×为。这句话,有两个版本,一个叫“无为而无不为”,一个叫“无为而无以为”。无为而无不为,意思很清楚:啥都不做,啥都做了。这是“假无为”。无为而无以为,意思也清楚:啥都不做,也不想做。这是“真无为”。老子说的,究竟是哪个?不知道。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是“无为而无不为”。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是“无为而无以为”。这就有点麻烦了。更麻烦的是,老子这话,两个地方都有,一个在第三十八章,一个在第四十八章。可是,《简本》有第四十八章,没有第三十八章。《帛书》刚好相反,有第三十八章,没有第四十八章。这可就怎么都说不清了。
表面上看,老子与韩非的区别很明显。韩非讲矛盾,老子无差别。韩非的名言,是“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韩非子·显学》)。一块冰和一块烧红的炭,能够长期放在一起吗?寒冷的冬天和酷热的夏天,能在同一时刻到来吗?不能。韩非还讲,一个人,不能同时卖矛又卖盾。因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结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总有一个要倒霉。这就是“矛盾”一词的来历,它的发明人就是韩非。
说不清,就只有猜。我的看法,是两句都有,只不过“无为而无不为”在第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以为”在第三十八章。也就是说,真无为,假无为,都是老子的思想。因为这两句话,也可以统一。啥都不做,也不想做,却啥都做了。不通吗?也通。
难讲的是庄子与韩非。
实际上,按照老子的思想方法,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老子的思想,也应该如此。或者说,老子的思想,就是一枚硬币。真无为和假无为,是它的两面。庄子看见了真无为的一面,韩非看到了假无为的一面。更何况,《老子》书中,原本就有“帝王南面之术”,还有兵法或兵道。这些内容被韩非接过来,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周易》是变革的哲学,《老子》是不变的哲学。孔子是中庸的哲学,老子是否定的哲学。这两个,都好讲。
可惜,韩非的立场,跟老子却是相反的。老子站在弱者一边。他的主张,可以说是“天择物竞,弱者生存”。韩非则站在强者一边。他的主张,可以说是“天择物竞,强者生存”。弱者才喜欢讲转化。因为他受压迫,被挤对,老在下面,总想咸鱼翻身呀!至少,也得寻找心理安慰。这就得说,小的好,弱的好,卑下的好。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不可一世,都不能长久,迟早会倒霉的。强者则喜欢讲斗争。反正,他有的是力量。你循循善诱也好,拐弯抹角也好,据理力争也好,他只用拳头说话。韩非的方法跟老子不同,也不奇怪。
老与孔,也不同。孔子讲中庸,老子唱反调。孔子的名言,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是说,修养与质朴,应该旗鼓相当,一家一半,恰如其分。老子的名言,则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说,祸当中有福,福当中有祸;祸会变成福,福会变成祸。祸一来,福就来了;福一来,祸就来了。因此,祸不是祸,福不是福。星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可见,孔子讲的中庸,是“你不吃我,我不吃你”,甚至“你让着我,我让着你”;老子唱的反调,是“你不是你,我不是我”,甚至“你才是我,我才是你”。
至于老子与庄子的区别,就不讲了。要讲,也只能说庄子是“真无为”,老子是“假无为”,或者既有“真无为”,又有“假无为”。但这无关紧要。反正,真无为也好,假无为也罢,都对后世产生了影响。老子的本意,就不重要了。陆游诗云:“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思想家的“死后是非”,就更没法管。你想嘛,《周易》和《孙子兵法》都跟企业管理挂钩了,我们又何必那么学究气呢?
再说老子与孔子。
不过,有为与无为的关系,倒是很有意思。排列组合一下,可以得出四个选项:以有为求有为,以无为求有为,以无为求无为,以有为求无为。以有为求有为,是墨子;以无为求有为,是韩非;以无为求无为,是庄子。那么,以有为求无为,又是谁呢?
先秦书,《老子》和《周易》是哲学意味最浓的。共同点,是都讲阴阳变化。但,《周易》喜欢变,《老子》不喜欢。《周易》认为,世界永远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有变是不变的。既然如此,就应该主动适应世界的变化,走在世界变化的前列,至少也要做到“与时俱进”。《老子》呢,也认为世界总在变。好事会变成坏事,坏事也会变成好事;美会变成丑,丑会变成美。不过在他看来,既然反正要变,我又何必变呢?要知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第二十三章),瞎折腾什么呀!更何况,“反者道之动”。现在变过去,下次还得变回来。总之,《周易》的主张,是“唯变不变,那就去变”;《老子》的想法,则是“既然会变,何必去变”。这是《老子》与《周易》的不同。
禅宗。
先说《老子》与《周易》。
禅宗,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要讲的,只不过是最后一讲。之前,要讲一下魏晋风度。为什么要讲魏晋风度呢?因为魏晋风度与《周易》、老子、庄子,都有关系。而且,从庄子的“以无为求无为”,到禅宗的“以有为求无为”,魏晋风度是一个中间环节。弄清楚了魏晋风度,就更能够理解禅宗了。
现在,老子的方法,就讲得差不多了。诸位大约已经看出,老子的思想,是很独特的。跟其他思想、其他智慧,区别也很大。如果比较一下,应该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