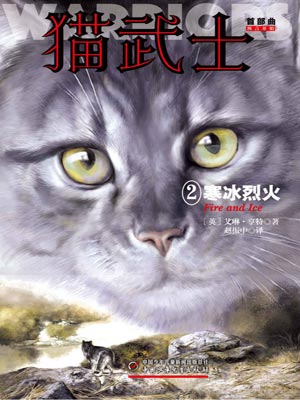柏瑞尔·马卡姆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但是,”他接着说,神情中父亲的担忧超越往常,“埃尔金顿家的那头狮子除外!”
这头埃尔金顿的狮子在农场周围方圆十二英里内闻名遐迩,因为,如果你恰好在这个范围里,就会听见它的嘶吼。它饿的时候会嘶吼,悲伤的时候会嘶吼,有时则仅仅想要嘶吼而已。假如,夜晚你毫无睡意地躺在床上,听见断断续续的声响传来,开始时听着像困在乞力马扎罗山谷的死亡幽灵在咆哮,结束时听着像这个幽灵突然逃脱枷锁来到你床边,你知道(因为有人告诉过你)那是帕蒂之歌。
那时,有两三个东非的殖民者抓到过狮子幼崽,并把它们养在笼子里。但是帕蒂,这头埃尔金顿家的狮子,从未见过任何笼子。
它已经长大,黄褐色皮毛,黑色狮鬃,无忧无虑。它以新鲜肉类为生,用不着它亲自动手。它醒着的时候(恰好是别人睡觉的时候),在埃尔金顿的原野和牧场上信步由缰,安逸得就像一位帝王漫步在他治下的花园中。
它活在孤寂之中。没有伴侣,却是一副漠然的样子,总是独来独往,无心经营实现不了的想象。它的自由并无物质的界限,但这片平原上其他的狮子,不会让一头沾染人类气息的狮子进入它们最在乎的族群。所以帕蒂吃、睡、咆哮,有时候或许还做梦,可它从不离开埃尔金顿。帕蒂是头被驯服的狮子,这千真万确。它对原野的呼唤充耳不闻。
“我总是很提防那头狮子,”我对父亲说,“但它真的没什么恶意,我曾看见埃尔金顿夫人抚摩它。”
“这不能证明任何事情。”父亲说,“一头被驯养的狮子就是头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狮子——而任何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事情都是不可信的。”
一旦父亲做出如此哲学意味浓郁,且如此广义的论断,我就知道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轻轻碰了碰马,然后我们骑着马慢跑过通往埃尔金顿农场的剩余路程。
这个农场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建在非洲的那些农场大,但有幢带宽阔走廊的漂亮房子。我父亲、吉姆·埃尔金顿、埃尔金顿夫人以及其他一两个拓荒者就坐在走廊上聊天,对我来说,他们的话题总是肃穆得不可思议。
他们会喝饮料,但更远一点的地方还有张摆设丰盛的茶桌,只有英国人才会这样铺张。后来,我有时会想起埃尔金顿家的茶桌——圆形、很大、白色,结实的桌腿立在花园内的绿色葡萄藤下,在距离非洲边缘一千英里的地方。
我想,它代表着某种认知而并非奢侈。它是件证据,证明英格兰仍因两样赠予而亏欠着古老中国——茶与火药,它们使扩张成为可能。
蛋糕和松饼没法贿赂我。那时我有自己的消遣,或者说矢志不移的期待。公正无私的记忆吝啬得不肯与我多做寒暄,我快步离开那所房子向前跑去。
我飞奔过埃尔金顿家房子后面约一百码处的方形干草棚,看见了毕肖恩·辛格,我父亲派他先过来照顾我们的马。
我想这个锡克人那时一定还不到四十岁,但他的脸永远都不会透露他的年纪。有时他看起来像三十岁,有时看起来又像五十,这要看天气、时间、他的心情,或是他头巾的倾斜度。要是他把胡须和头发分开,剃了胡子并剪头发,那他活像吉卜林笔下的大象男孩,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但他从不剃胡子也不剪头发,所以,起码对我来说,他一直是个神秘人。不算年轻也不算老,却历经沧桑,就像漂泊的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