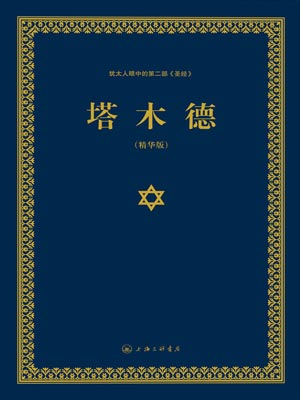夏立君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高度概括了二十四岁前的人生:
商鞅、荆轲、项羽、蒙恬、白起、吴起、屈原、贾谊、李斯、李广、李陵、张汤、主父偃等等,从市井细民到宫廷权要,他们的人生无不以悲剧收场。
比生活在这个时代更加幸运的或许是:司马迁有一位伟大父亲——史学家司马谈,一个有能力有条件站在时代文化巅峰的人物。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令掌文史星历。“天下遗文古事,无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读书条件当世无人能比。司马谈服膺道家精神,却让儿子师从孔安国、董仲舒等人习儒。这应当含有为儿子规划未来人生的现实考虑。崇儒大局已定,只有习儒才能走上仕途,这类似今日的接受应试教育。司马迁十岁时,父亲就将他从家乡夏阳(今陕西韩城)带到京城长安。二十岁时,司马迁迎来了他一生至关重要的首次壮游。这时的司马迁无公职,出游必出于父亲的安排。由此可见司马谈对儿子的期待之深。司马谈的影响及有意识的培养,必使司马迁的文化自觉、史学胆识发育极早,为他成长为精神更雄伟、文采更丰富的人,奠定了重要基础。
李斯:出卖良知、精神自宫者的典型。精神自宫者死于阉人赵高之手。这是个掀动司马迁复杂情感的人物,恶心、痛惜、怜悯,皆有之。《李斯列传》中,司马迁开篇就让李斯面对老鼠——蝇营狗苟的老鼠。这是一位身体被阉割者,给一位精神自宫者的定位。李斯作为一个携有巨量信息的人物,出现在司马迁笔下。
司马迁(公元前约145——前87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的命运,他的才华,在此时空下展开。
张汤:一个“模范”酷吏而最终不得不自杀。《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亦开篇就让张汤面对老鼠。张汤儿时,肉为鼠偷吃,张汤因看家不力遭父殴打,张汤怒而掘穴捕鼠,煞有介事布置场面,传布文书庄严“审鼠”,当堂处鼠以“磔刑”。审鼠的孩子后成长为酷吏。这个盛世看上去光鲜异常,却需要大量酷吏来维稳。《酷吏列传》所描绘的恐怖世界是皇权的投影。纣只有一个,助纣为虐者却必是一群。张汤审鼠,庄严常常就是滑稽。
大文明需要大时空。汉朝人不论走多远,都没有发现文明高于自己的地方,更不会发现比自己还要庞大的帝国。在这一大背景下,刘彻追求好马的热情极为高涨,为此他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派将士一次又一次深入西域。后世不断有人诟病刘彻此举。其实,这类似当今追求尖端武器。刘彻有理由认为,他最有资格拥有尖端武器,最好的马应该为他的帝国驰骋。
张汤、李斯与鼠之关系这种细节,极具黑色幽默味道了。
这些人与司马迁同代。他们大都不会留意、在意人微言轻的司马迁,而早早就有史学使命意识的司马迁却不会不留意他们。
主父偃:一个皇权时代庸常官僚的庸常悲剧。司马迁却对之寄慨遥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写至主父偃被族,司马迁悲情又起:“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这一徽记,如伏流千里,贯穿《史记》全书。
……
司马迁以文学笔法入史,后世对此争议不断。司马迁之所以首创纪传体修史体例,既决定于他的实录精神,亦决定于他将文采“表于后”的决心。这一体例最有利于塑造人物,铺陈他非凡的文采。李斯面对厕中鼠与官仓鼠的心理活动,小儿张汤一人在家中审鼠的场景,鸿门宴上的勾心斗角,项羽乌江自刎时言行……《史记》中遍布此类私密性极强的细节。这类细节是怎么来的?我倒宁愿相信,有些细节干脆就来自司马迁的伟大文学才能。这违背历史真实了吗?司马迁追求的是另一个层面上的真实,更本质的真实。把历史场面生动地布置在你眼前,这是司马迁突出的本领。一个无史识史才的人,给他再多史料也无意义。《史记》是史诗,亦是诗史。它同时具备伟大诗篇的美学意义。
董仲舒,首次确立儒学至尊地位的思想家。天下一统了,也必然要求“软件”一统。帝国到了从容建设“软件”的时候,董仲舒应运而生。他将儒学世俗化、实用化兼神学化,殚精竭虑从天上到人间为体制寻找自圆其说的合法性。
司马迁笔下的现当代人与古人,味道完全不一样。写古人,虽也有激情澎湃之时,但以求证、概括、理性为主。写现当代人,司马迁可就放开手脚了。你看,陈胜、吴广、项羽、樊哙、刘邦等等一个个活灵活现,像极了小说中的人物。司马迁是一个有强烈还原历史真实愿望的史学家,又是一个具有非凡创作能力的伟大文学家。“正是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罗素《西方哲学史》)我们当然亦可对司马迁持此态度。可是具体到《史记》中的历史事实与细节,相信还是怀疑,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并且也不再是重要问题。以情感入史,是司马迁的缺陷,也是他的伟大。去掉司马迁情感的《史记》,绝不会是伟大作品。司马迁对距他不远的现代人物,敢于进行创造、塑造,大肆张扬文采,那是他自信已充分占有材料,对人物具有本质性把握。他在记录历史,同时实现了艺术真实。
张骞,中国古代走得最远、出使时间最长的外交家、旅行家。军事将领向远方伸出铁拳,大汉使者则向远方传布帝国消息。
司马迁所创制体例为后世继承,其著史的本质精神却难以为继。幸运的是,司马迁的文学精神却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文章大家,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无不以《史记》为准绳。当文风颓靡时,真正的文学家就到司马迁那里寻找生机和力量。从《红楼梦》的浓厚悲剧氛围里,亦可探得《史记》消息。伟大的文化创造必息息相通。
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在现实与历史中,他们皆赫赫有名。他们一次又一次远征漠北、西域。他们是武帝性格的延伸,是帝国挥出的铁拳。对内集权与对外征伐,是刘彻的力量来源。他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武帝一朝,是中国古代进攻型将领最多的朝代。靠蛮力挑战汉朝的匈奴,在武帝铁拳不断打击之下,不得不一再远遁。
司马迁职掌文史星历,著史却是私人撰述。至东汉班固时,已是奉旨修史了。私著未必能超越精神阉割,奉旨却是必须先行精神阉割的。相对于《史记》,《汉书》是规矩的皇家史册。《汉书》主旨或许可如此概括:明天人感应,固皇权一统,成官史规范。核心是“以求亲媚于主上”。班固判断《史记》,就完全是以“真理在握”的眼光了:“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班固眼里,司马迁俨然异端了。大师往往充满矛盾,精神阉割者却最易以立场坚定,真理在握面目出现。班固肯定《史记》实录精神,却难以接受其思想锋芒。班固的话对皇权后世影响甚大。汉末,司徒王允欲诛蔡邕,蔡邕上书求毁容刖足,留下一条命,以著成汉史。这显然是要效法司马迁了。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蔡邕列传》)蔡邕难逃一死。《史记》为谤书说在两汉甚为流行,这是将司马迁发愤著书降低为“泄愤著书”了。司马迁不论是否心存诽谤,只要他贯彻实录精神,其当代及后世必有人视之为诽谤。司马迁恪守实录,但又有强烈的主观性、个性。终身抱持婢妾心态的大小班固,必然不能仰见司马迁的瑰异光彩。与《史记》相比,后来二十余史无不热衷于为皇权“资治”,少有社会经济大局的揭示,更乏对人性的深度探究,显然气量狭窄,局促矮小。无主观性、个性之史学家,竟亦难以实现深远的客观性。
一号人物当然是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刘彻十六岁登基,在位逾半个世纪,将汉朝推至鼎盛,寿命长,威势重,能量大,阴影亦大。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刘彻出巡至河东郡(今山西夏县),郡太守料不到突然来了皇上,供给保障措手不及,急得以自杀来逃避。司马迁以十一个字实录此事:“河东守不意行至,不办,自杀。”(《史记·平准书》)第二年,同样原因,陇西郡守自杀。皇上——这个权力恐龙,影子就能吓死人。刘彻热衷武功与出巡,是古代走得最远出巡次数最多的皇帝。他对女人的热衷亦甚有名。“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翦伯赞语)
针对班固贬斥司马迁之言,明代思想家李贽说:“不是非谬于圣人,何足以为迁乎?”“《史记》者,迁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为一人之独见也者,信非班氏所能窥也欤。”(李贽《藏书》卷四十《司马谈 司马迁》)可谓一语中的。班固眼中的“蔽”,正是《史记》光辉所在。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司马迁暗讽的主箭靶。刘彻创造了一个无人敢判断他的时代,司马迁却给他一个判断。从维护统治者光荣形象的立场来说,《史记》为谤书说当然是成立的。对以天生正确自居的人或事物来说,你只要讲真话就完全有可能被视为诽谤。写刘彻父亲的《孝景本纪》、写刘彻的《今上本纪》,被从《史记》中删除,亦可证此点。睥睨千古易,判断当代难。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对当代史的忌讳几乎是天然的。更有甚者,对古代史都是如此。
看看这样一个时代,容纳了些什么人物。
深情的司马迁“绝情”于其所处的时代,不如此,他不会走向雄伟开阔。
汉初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饱经战乱的社会得到休养生息。第五位皇帝汉武帝刘彻接手的是一个富于生机、野心勃勃的庞大帝国。这个帝国,差不多可说就是从前的“天下”。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所向往的天下一统局面,似乎是实现了。
有此绝情,方有绝唱。有此绝唱,方能称为“独断历史”(章学诚语)。
人是历史动物。把自己安顿在历史里,是人类由来已久的精神需求。汉武帝时代,中华民族已累积了丰富的历史经历。而历史文化最丰富的家族就是司马迁家族。司马氏世代为史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