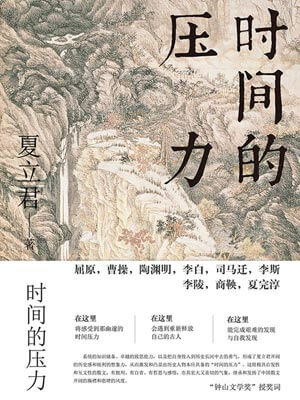为悲剧性的乐观主义辩护 (第1/5页)
维克多·E·弗兰克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在一家综合性医院神经官能症科工作了25年,亲眼目睹了病人们能够将自己的困苦转化为人类成就的能力。此外,我们也能找到经验证据以支持这种人可以在痛苦中发现意义的可能性。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 “对那些公开表示被俘期间虽然感到非常紧张——充满了虐待、疾病和营养不良及单独监禁——但是仍然从被俘经验中获得有益启发的越战战俘的数量之多感到吃惊”。
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个途径:即使是处于绝境的无助受害人,面对无法改变的厄运,仍能自我超越,并且以此改变自己。他能够把个人悲剧转化为胜利。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就表示希望意义疗法 “可以帮助人们抵抗20世纪美国文化中某些不健康的潮流,在这种文化中,不可治愈的受害者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痛苦感到骄傲,而认为它是耻辱,这导致他们不但不幸福,还为自己的不幸感到羞耻”。
但是,“悲剧性的乐观主义”最有力的论据是拉丁文所谓的 “偏见式论证”。比如,杰里朗就是 “人类大无畏的精神力量”活生生的例证。援引 《德克萨克纳报》的报道:“三年前,杰里朗因一场车祸造成脖子以下高位截瘫,当时他只有17岁。今天,他能够用嘴叼着笔写字。他通过特制的电话参加了社区大学两门课程的学习。他通过闭路电视能够听课并参与课堂讨论。他还花了大量时间阅读、看电视和写作。”我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觉得生活富有意义和目标。我在差点儿丧命的那一天采取的态度成了我对待生活的座右铭:我虽然折断了脖子,但我没有被生活打倒。我已经申请了第一门大学心理学课程。我相信,残疾只会增强我帮助他人的能力。我知道,如果没有那场灾难,我是不可能取得这样的进步的。”
正如意义疗法所宣扬的,找到生命之意义有三个主要途径。第一是创造或从事某种工作。第二是经历某种事情或者面对某个人,换句话说,不仅能从工作中也能从爱中找到意义。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就发现意义疗法中 “体验同成功一样都具有价值的观念,是具有治疗作用的,因为它纠正了我们过度强调以内心经验为代价而获得外部成功的做法”。
这是不是说,要发现生命的意义,痛苦是不可或缺的呢?不是。我只是坚持一点:尽管痛苦是存在的,甚至说可以通过痛苦找到意义,条件是痛苦难以避免,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说。如果它是能够避免的,那么消除它的原因才是有意义的事,因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与其说是英雄行为,不如说是自虐。另一方面,如果你不能改变造成你痛苦的处境,那你仍然可以选择采取何种态度。残疾不是杰里朗选择的,但他选择了不让厄运摧垮自己。
那么,人是如何找到意义的呢?正如夏洛特·布勒尔所说:“我们能做的,不过是研究那些看来找到了生命意义的人和那些没有找到这种意义的人的生活。”除了这种图画式的方法,我们还可以采用生物学方法。意义疗法认为,良知是一种提示器,能够指示我们在特定情境中前进的方向。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良知必须仔细衡量所处情境,按照一套标准和价值系统去评价它。但是,这些价值不能在意识层面上被我们发掘和采用,它们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它们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积淀下来,以生物进化为基础,植根于生物学深处。康拉德·洛伦兹可能抱有类似的想法,他曾提出 “生物学优先”的概念,当讨论我关于价值形成过程之生物性基础的观点时,他饶有兴趣地表达了自己的共鸣。无论如何,假如价值论的自我理解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假定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物学遗传之中。
如我们所见,首要的是创造性地去改变让我们遭受磨难的境遇。但最要紧的还是要知道如何承受不可避免的痛苦。实验性的证据表明,普通人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奥地利民意调查机构最近报告说,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最受尊敬的人既非艺术家也非科学家、政治家或体育明星,而是那些昂首征服厄运的人。
事实仍然是,从意义疗法的角度看,意义及对意义的认识完全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或是藏在象牙塔里的。我对意义的认识——个人对特定情境的认识——介于卡尔·布勒尔概念中的 “阿哈体验”与马克斯·维黑莫尔理论中 “完形概念”的中间地带。对意义的认识与经典的 “完形”不同,因为后者意味着某个“人”在 “某个地方”的突然领悟。而对意义的认识在我看来最实在不过,就是意识到了现实背景下的某种可能性,或者通俗地说,意识到在给定情境下 “能够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