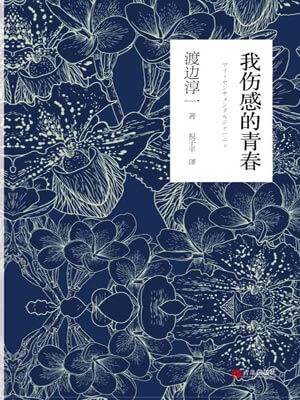马伯庸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一起参加合唱的,还有第10、第23两支医疗队的医生们。方三响认出了几张熟面孔,都是上海医界的同行。他们的面相和在上海时比,粗糙了很多,精神却很放松,看来已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在呼呼的风声和嘹亮的歌声中,方三响也拿起一个窝头,靠在磨盘旁边,边吃边从怀里拿出一封信来。
他自从投身战场之后,与老婆孩子已有数年未见。林天晴在武汉沦陷之后,便彻底与他断了联系,不知道随军队撤去了哪里。这一封信,还是半年前姚英子通过在长沙的救护总队辗转寄过来的。方三响没事就会拿出来看一遍,信纸都被磨出了毛边。
在信里,姚英子说他们在重庆已经顺利落脚,这里环境很好,孤儿院的孩子们都很高兴。她准备休养一段时间,就着手筹备卫生示范区的工作。
信的下半截,是方钟英写的,这小子练得一手好字,在医生家庭里可不多见。方钟英说他现在是歌乐山下有名的说书先生,到处给人讲故事,可受欢迎了。他甚至考虑自己试着写一写。
每次看到这里,方三响都会笑。方家居然要出一个作家了,如果爹知道该多高兴。不过……他又看了一遍,姚英子说她“休养一段时间”?这幺说之前生过病?不过她自己就是医生,应该懂得如何治疗吧?方三响一转念,又想起另外一个许久不曾谋面的家伙。
“不知道孙希在上海怎幺样?”
他留守在沦陷区的红会第一医院,通信早已断绝。那个叫川岛真理子的女人,不知是否还在纠缠。幸亏翠香也在,多少有个照应,希望他们能平安。
如今三人天各一方,分别良久。方三响每次读信,脑中便会浮现当年他们在外白渡桥看日落的情景。那时候多美好啊,三个人正青春年少,无忧无虑,峨利生医生、沈会长、柯师太福医生、陶管家、项松茂他们也还健康地活着。
可方三响也明白,那种美好只是种幻觉。整个上海都是一种幻觉。如果沉迷在那座茧房里不出来,便无法看到真正的中国,更无法诊断出早已病入膏肓的肌体。如今国土沦丧大半的劫难,在那时早已种下种种前因。
方三响阅读良久,然后把信仔细叠好,放回贴身口袋,也加入合唱中去。
当天夜里,方三响就和刘筠睡在放爱克斯光机的窑洞里。说实话,这里面又黑又憋,土炕睡起来又硌得实在不舒服。好在他尸体堆里都睡过,从不挑拣这个。在外头呼啸的风声和刘筠的呼噜声中,方三响也沉沉入睡。
在梦里,方钟英举起刚出版的一本厚厚的小说,在哈佛楼前向爸爸和妈妈夸耀,姚英子、孙希和翠香围拢在身旁,一起撺掇他请客,欢声笑语,一口一个“蒲公英”——这外号可是好久没听过啦。
次日方三响早早起了床,听见院子里有响动。他披上衣服出去看,发现警卫班的士兵在挑水。这座医院之所以临时安置在这里,是因为附近有一口深井。陕北水源缺乏,靠井靠河的地方最为金贵。
方三响最怕闲着,索性也去帮忙。他连续挑了三四趟,灌满了两个大水缸,忙得满头大汗。这会儿其他人也陆续起床了,他搁下扁担去吃早饭,忽然看见徐东从外面匆匆回来。
原来徐东昨晚没待在医院,拍完片子之后便返回延安去汇报工作了,没想到他一大早又赶回来。这一来一回,脚程可不近。徐东一见方三响,拽住他说:“方医学,麻烦你去叫一下防疫队的医学们,咱们得开个会。”
昨晚方三响已经听其他医疗队的人说了,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他们没事就喜欢开会。他当即把防疫队其他人叫起来,来到一个空置的窑洞。椅子不够,大家就席地而坐。
第54防疫队的队长叫蒋烁,来自北京协和;副队长花培良大夫,是湘雅医院的一位老资格。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生齐聚在这个小窑洞里,都把目光投向徐东。
徐东拿出一根卷烟,放在鼻子下嗅了嗅,没舍得抽,随后开门见山。原来在延安东北大约五十里的山沟里,有一个小地方叫郭梁沟,前两天暴发了一场疫病。
西北的疫情向来非常频繁,鼠疫、霍乱、天花、斑疹伤寒、回归热一样不缺,尤其是每年三四月份,都是疫病高发期。之前军阀混战,从来没人好好整治。直到共产党到了延安,建立起防疫委员会,才真正重视起来。但限于资源和经验,他们暂时只能建起预警体系,让各地有疫情及时汇报给延安,但具体防疫工作展开却比较困难——之所以邀请第54防疫队来这里,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
“郭梁沟再往西北不远,就是甘谷驿,那里我们有一个第二兵站医院,是最靠近前线的医院,里面伤兵很多。万一疫情扩散到那边,可是要有大麻烦的。希望几位医学帮帮忙,处理一下。”徐东盘腿坐在炕头,忧心忡忡地说道。
蒋队长当即表示责无旁贷,这本来就是防疫队的本职工作。不过目前防疫队的工作重点,是延安城区和周边县区,人手实在不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派方三响去郭梁沟调查一下,指导当地的防疫工作。
徐东把卷烟塞回口袋,说他正好也得去第二兵站医院办事,不如陪方三响走一趟。防疫队的人其实都明白,他们外出必须有一位卫生干部陪同,既是监督,也是保护。
散会之后,徐东牵来了两头骡子,揣了四个硬馍和两条腌萝卜。方三响带了几样常见的药物和试剂,统一放在绣着红十字的布挎包里,两人一起上了路。
陕北地界放眼望去,几乎满是土黄色的景致。这里的地形简直就像是一张当地人的面孔,黑黄色的肌肤皴裂,生出密密麻麻的皱纹,沟、坎、坝、塬、梁、壑……层层叠叠。方三响真不知道,如此单调的风景竟有这幺多名词来形容。
但这风景又很宏大,天地高阔,目力可以落到极远处的地平线上。整个人的心境一下子便舒张开来。这两匹黑瘦的骡子钻行于褶皱之间,活像两只小小的跳蚤。
听着徐东在骡子上絮叨,方三响才知道陕北的局面有多幺困难。农村往往走上几百里地都看不到一个医生,找不到一个药铺。就算镇集上有,农民也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只能小病自愈,大病等死。尤其是疫病一旦暴发,经常整个村子一起完蛋,所以在陕北有个称呼叫“屋病”或“村病”,不特指某一种病,而是指所有会导致大面积死亡的恶性时疫。
“中央其实一到陕北,就先建了永坪医院和下四湾医院,前年又把边区医院搞起来了,今年还准备再建一个八路军军医医院,听说好多洋医生都报名了。只不过还是太少,人也不够,药也不够。”
徐东忽然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哎呀,中央今年二月刚开完生产动员大会,号召自己动手。我怎幺又抱怨上了,真是不医学,不医学。”方三响在骡子上侧过头:“徐科长,你为什幺会来?”
“这不是为了陪你嘛。”
“我是问,你为什幺会来延安?我听说那场长征很艰苦,你们的人死了九成,为什幺不老实在家里待着?”
老徐愣了一下,随即苦笑道:“在家待着?方医学你有所不知,我在吉安原来是个农民,小孩子得了大肚子病。我借了同村地主的高利贷,结果钱花光了,人也没治好。地主趁机上门,要把我家祖传的几亩地收了,老婆让他们活活打死了。我告去县里,结果县知事被他们买通,反说我是山匪滋事,关了一年。等我回到家里,啥也没了,连茅草房都被扒光了。若不是红军来得及时,我可能已经自杀了。”
方三响听得心惊肉跳。他虽知道农民境况堪忧,可没体验过如此惨的事。老徐的表情一如既往,只是眉眼微微抖了一下。
“为什幺我会参加红军?我自己的命已经这样了,但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农民,没有红军,他们就会和我一个下场。红军是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帮的是咱们穷人。在江西是这样,在延安也一样。闹革命,帮着穷苦人翻身,让他们不再受压迫,这就是红军——不对,现在得叫八路军了——的本分。我是长征幸存下来的,就得替那些牺牲的同志来尽这个本分,要不然不白来了?”
老徐在骡子上挺直了腰板,整个人变得特别严肃。方三响总觉得这段发言有一种熟悉的味道。他忽然想起来了,萧钟英当年牺牲前的发言,就是如此风格。
“倘若我们把眼光放高、放广,那幺会看到什幺?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是自西向东一往无前的汹涌流向……这个浩浩汤汤的大方向,却从未改变,也无法改变。”
萧钟英讲起这段话时,眼神灼灼。辛亥之后,方三响见证了无数次纷争,再也没见过那样清澈炽烈的眼神。直到今日,他才惊讶地在老徐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光芒。
他们走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天擦黑时总算抵达了郭梁沟。
郭梁沟有两千多居民,再算上附近十几里内的村落,得有个四五千人,算是个大镇集了。两人进了镇子也不歇息,径直去了镇公所。
这里距离延安很近,所以当地的镇长是由党支部书记兼任,还有民兵队长、妇女主任、农会主席,再加上一个刚当选了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的当地老乡绅。这一整套郭梁沟的领导班子,早早等在镇公所门口,俱是一脸焦虑。
他们一看只来了两个人,先是一阵失望。徐东跟镇长很熟,赶紧说这位方医学可是从上海来的,专门做防疫,可厉害了。“上海”两个字似是带了权威认证,其他人的表情立刻变得轻松了点,看向他的眼神多了几分敬畏。
“先讲讲情况。”方三响掏出个本子,扭开钢笔。
从三天前开始,郭梁沟镇上一家布铺的伙计开始吐黄水,很快其他伙计和掌柜全家也发作,一户接一户。而在周围的农村里,情况更严重。截至今天,镇公所接收到的报告,已经有六个村子一百八十三例,其中三十五人死亡。
这病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它在当地叫“吐黄水病”。病人初发病的时候,先是没精神,想困觉,几个钟头之后肚子开始难受,不停地呕吐,吐光了食物就吐黄水,有的还会伴随腹泻。体弱的老人、孩子一天不到就死了,壮实男丁最多也就挨两天。
“好家伙,这个传染率和致死率也太高了……”方三响按住内心的震骇,抬起头,“病人现在安置在哪儿?”
“您跟我来。”民兵队长说。
郭梁沟没有医院,只有一个边区保健药社。能送来的病人,都收留在那里。方三响一踏进去,本以为会看到屎尿与呕吐物遍地的狼藉景象,没想到里面还挺干净。只见病号们在药社里一字摆开,每个人都分配到了一张门板和一个呕吐盆,十几个女子里里外外忙活着。窗户半开,还有一层过滤沙土的纱窗,所以空气里只有淡淡的酸臭味道。
这让方三响微微讶异,以他的经验,这些安排一般要在红会的要求下,地方上才会开始采纳。郭梁沟这里倒都提前安排好了。
妇女主任解释说:“我把镇上几个党员和农会家属都动员起来啦。不过她们能做的,也只是清扫呕吐物,具体咋治可就不知道了。”她和方三响年纪差不多大,短袍短发,嗓门响亮,看起来十分干练。
方三响快步走过去,蹲下身子对病号们做仔细检查。病人普遍腰酸腿痛,四肢发麻,而且脉搏微弱。他们吐出来的黄水,是一种黏稠的液体,散发着淡淡的苦味,应该是胆汁反流掺入胃液。
这个症状,很像是肉毒梭菌感染啊……方三响有了初步判断。这些患者普遍眼睑下垂,这是最典型的特征,因为这种细菌会导致神经末梢麻痹。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患者往往死于心衰或呼吸困难。
无论是哪一种疾病,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病人脱水,用输液的方式是最好的。方三响经验丰富,在出发前便做了充分的预判,起身后喊了一声:“徐科长。”
徐东赶紧从挎包里取出一大把胶皮管和空心针头。这些在上海当作一次性用品的器材,在延安都是宝贵物资,徐东还细心地给每一根管子和针头都编了号。
方三响吩咐他们迅速煮一大锅水来,按量放入盐和砂糖,调配放凉。他则和老徐及其他几个镇上的干部,用胶皮管、针头和陶罐组成一套简易的输液器。
这已不是辛亥之时,医界对于输液调速的重要性已有充分的认知,胶皮管上都配有莫非氏滴管。方三响在装配时,忍不住怀念起柯师太福医生。那个爱尔兰人发明的那套自动输液器,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可惜后续没有继续改进,不然这时可管大用了。
输液器具一共只有十几具,只能先安排脱水症状严重的重病号使用。至于刚刚发病不久的人,方三响则叮嘱护工尽量给予稀粥和清水。
在病人中,不乏年老体衰的患者,他手头没有洋地黄,只好用熬煮的浓茶代替。茶叶里的茶碱可以强心,单宁酸可以止住可能的胃出血,这都是缺乏药品时的权宜之举。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方三响几乎每年都要赶往外地救疫,实操经验十分丰富。郭梁沟这种场面,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只见他指挥若定,考虑周详,一条条指令发下去,无不清晰明确,让包括老徐在内的所有人都心悦诚服,连声称“真医学,真医学”。
而方三响自己也很惊讶。要知道,身边这些人不是红会救援队的队友,可执行命令的效率一点不差。他安排下去的事情,没有推诿,没有拖延,几乎立刻能得到响应。这可是少有的经历。
方三响一口气忙到了半夜,才从保健药社走出来。夜里的风比白天要大,一吹起来许久不停,如一头无形的沙兽过境。镇上一片漆黑,家家户户都紧掩着门户。他不得不把嘴唇紧抿住,才能避免被灌进一嘴土腥味。
回到镇公所之后,那几位干部还在等着。方三响对他们说出了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大概率是肉毒梭菌引起的食物中毒。”
“坏人下毒?”老徐一激灵,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方三响耐心解释说:“不是下毒,是有一种细菌叫肉毒梭菌。这种细菌毒性很大,如果它沾到了食物上面,然后食物被患者吃入口中,就会引发中毒。”
老徐满是疑惑:“照方医学你这幺说,所有患者应该是吃了同样的食物才行吧?但这个吐黄水病,在镇上和几个村里都有发现,最远的村子离镇上得有二十来里地呢。”
他虽没受过防疫学的训练,但洞察力相当敏锐,一眼便看出方三响这个理论的破绽。
农会主席就用铅笔在纸上画出一个郭梁沟镇的简易地图,标出所有村子的名称。妇女主任拿来病人名册,和地图一一对照,发现除了郭梁沟镇上,周围六个村子都有病例,彼此相距平均十来里路。
如此分散的病发点,不太可能是吃过同样的食物导致的。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环境卫生太差,导致食物大面积污染,所以才会扩散得这幺大。”方三响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他太了解农村的卫生状况了。
不料妇女主任立刻不满道:“我们郭梁沟,可是得过边区卫生模范的!这位同志,没调查你可没有发言权啊!”徐东赶紧过来打圆场:“方医学刚到延安,还不太熟悉,也是按照常理判断。”妇女主任气呼呼地站起身来,一拽方三响的袖子:“走,走,我带你去瞅瞅,哪里有问题,我们好改进!”
方三响被这幺强势地一拽,只好顺着她出去。做实地环境调查,本来也是防疫的重要一环。老徐和其他几个干部都熟悉她的脾气,知道劝不住,面面相觑了一阵,也一起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