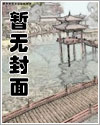第五章 教皇使团和康熙派出的洋钦差 (第1/5页)
孙立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但是清宫留下来一些零散文件显示,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多罗住在北京的大半年中,康熙都没有提到过礼仪问题。就是在《北京纪事》中,耶稣会神父的记录也表明,在正式的辞行会上,康熙也没有提到过礼仪问题,而只是多罗要求康熙给他一封官函,他好带回欧洲复命。康熙让多罗第二天再来,而在这个临时增加的会见中,康熙提到了中国礼仪问题。《北京纪事》其实又有意省略了一个重要的下午,就是辞行会结束以后到第二天临时增加的见面会中间发生的事。这个下午康熙在思考应该如何答复多罗要一封正式信函的要求,如果要写这封信,应该写什么内容。耶稣会神父是北京城中康熙唯一能找来探讨的人。《北京纪事》完全没有提康熙那天下午和谁讨论这件事了。而当时整个北京只有耶稣会神父有兴趣讨论中国礼仪问题。他们一直想找多罗谈,但是多罗一直回避。直到康熙和多罗正式辞行会结束,耶稣会神父都还没有和多罗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真正说上话。这时候,耶稣会神父只有靠康熙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多罗。因而我们看到,在第二天增加的会见上,康熙突然向多罗提出了中国礼仪问题。
《北京纪事》有目的地省略某些内容,来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意思,这其实就是中国历史书写中所谓春秋笔法中的“笔削”。写什么、不写什么或者说“削”去什么,都自有目的。《史记》中司马迁评论孔子作《春秋》时有意省略一些东西,评语就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耶稣会神父用春秋笔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欧洲的读者认为是大清皇帝自己要对中国的礼仪问题发表意见。而且他们还要让欧洲读者相信,康熙后来对中国礼仪问题很有意见,是因为多罗的处理不当导致的。客观地说,耶稣会神父的《北京纪事》达到了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后来的学者也确实相信康熙是被自大、自负的多罗带进了礼仪之争中。53
耶稣会神父能把康熙的注意力引到中国礼仪问题上去,靠的是他们与康熙的特殊关系,这不仅让他们能在康熙面前说上话,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们知道康熙会为他们出面。其实在把问题推给康熙之前,他们早就利用在内务府的关系让其他人为他们出面过。比如当时管理内务府的大皇子就出面问过多罗关于礼仪方面的问题。了解清史的都知道,康熙的大皇子是康熙儿子中没有多少文化,也对文化问题不感兴趣的一位。所以他出面向多罗提中国礼仪这样的学术问题,多半是传教士拜托他提出的,而不是他自己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兴趣。多罗有一次还对耶稣会神父发火,问他们为什么要把天主教内部的争论讲给异教徒。多罗所谓的异教徒就是康熙身边负责和他接洽的奴才。多罗责问耶稣会神父,难道他们认为他会听不出来哪些论点是那个奴才自己的,哪些论点是他们教那个奴才说的?54北京耶稣会神父看起来是西洋人,但实际上北京是他们的主场,内务府的人就是他们的人。
康熙是被耶稣会神父引到天主教内部的中国礼仪之争去的。他们希望通过康熙来向罗马施压,让罗马在这个问题上让步。50不过,耶稣会神父大约心里也知道把康熙这个教外皇帝引到自己的教内纷争中是不对的。所以,在记录多罗来华的《北京纪事》(The Acta Pekinensia)中,他们一直有意识地在淡化他们把康熙引向了中国礼仪问题这点。他们希望看记录的欧洲读者认为是康熙自己发现了礼仪之争的问题,因而参与了进来。但零散的清宫档案显示事情并非如此,康熙不是自已注意到礼仪问题争论的。在《北京纪事》中,耶稣会神父详细记录了他们是如何跪下来恳求康熙接见多罗,而且还把安多神父请求康熙的奏折完整翻译了出来;但对于康熙的回复,他们只翻译了一小段。5康熙回复的全文还在。52看完全文,就能知道,传教士是有意回避把全文翻译出来。他们省略没有翻译的部分,就是康熙猜测使节来华目的的部分。这部分就可以看出康熙完全没有想到过中国礼仪问题,他猜测多罗来华是为了处理耶稣会传教士的内部矛盾的。《北京纪事》记录的风格是尽量不遗漏任何细节。为什么要有意识地隐去这部分呢?因为这部分正好说明了康熙开始时根本没有关注过礼仪问题。
同时,耶稣会神父不想让康熙知道的内容,康熙就不知道。比如,多罗对于耶稣会神父在中国买田置地、赚取租金的做法就很有意见。而且认为他们与租户、佃户签订的租赁条款的很多细节是有违天主教教义的。为这些租赁条约,多罗和耶稣会神父争论过很多次。耶稣会神父把争论内容详细记录在《北京纪事》中发回了欧洲。55但是这部分内容,康熙就完全不知道,也没有过问过。按理说,这还不完全是他们教内之事,因为租赁关系中的佃户等,不是天主教徒,是大清内部的普通百姓。尽管这才是多罗和耶稣会神父在北京期间真正争论过的内容,但康熙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发表过意见。这说明哪些东西要康熙知道,要康熙出面,实际是完全掌握在耶稣会神父手中的。
康熙在多罗到来之前,对欧洲进行的中国礼仪之争并没有特别关注过。他可能或多或少从耶稣会神父那里听到过一些风声,但他没有想到多罗到中国来是处理中国礼仪问题的。对于这一点,现在存世的满文折子就是证明。在知道多罗来华以后,在外打猎的康熙多次写信让赫世亨询问耶稣会神父多罗来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康熙对多罗来华的目的有过各种猜测,但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中国礼仪问题。在接见多罗的会谈中,康熙也没有提过礼仪问题。
《北京纪事》中,耶稣会神父还有意把多罗塑造成一个性格不好、脾气暴躁、让人讨厌的人。但根据清宫材料来看,康熙对多罗并没有什么意见。康熙和多罗的私下交流更像现在朋友之间的交流,他多次让御膳房给多罗送吃的,多罗有病之时,还为他安排医生,为他找药。同时,他还几次问多罗有没有西药可以给他,还问多罗要过巧克力。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他们友好交流的证明。而且,康熙在写给他身边奴才的一份御旨中就明说:
传教士笔下的历史
览多罗汉字奏稿,似并无大逆之处。唯因尔等究诘的太厉害,故伊以为尔等向此处西洋之人·····.56
但耶稣会神父也有他们的想法。首先,耶稣会是天主教中最有学问的一个团体,能进入耶稣会的神父都是被考核过的。他们一个个都自视甚高,在很多问题上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才是正确的。公正地说,单从耶稣会神父学习中文的能力来看,他们确实都很厉害,其他教会的神父很难和他们相提并论。这些在华的耶稣会神父其实就是第一代的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的问题,他们认为他们才是天主教世界最了解中国、精通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人,所以教皇应该听他们解释中国传统礼仪。在他们看来,现在教皇禁止中国礼仪活动,是因为教皇被那些对中国一知半解的伪中国通误导了。其次,从历史上看,耶稣会神父以前通过他们的才学也确实改变过教皇的决定,这也让他们对再次改变教皇的决定有信心。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1574-1655)就下旨禁止中国教徒继续参与中国礼仪活动。“在浙江的耶稣会神父卫匡国1653年回到欧洲解释了中国礼仪问题,把中国的各种礼仪活动解释为世俗活动,不具备宗教意识。也就是说,这些活动和一神论的天主教并不冲突。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七世(1599-1667)就认同了卫匡国的说法,并下旨允准了中国的礼仪活动。卫匡国神父本身当然也是奇才,他回欧洲前在浙江传教,和江南士人多有往来。他在回欧洲的船上,凭着记忆一口气写出了三本书,回到欧洲就出版-三本书都是当时的畅销书。对于耶稣会神父来说,有卫匡国神父凭一己之力扭转教皇态度的先例,他们这次也对改变教皇抱有希望。也就是说,在多罗来的时候,耶稣会神父一开始想的,就不是如何接受和执行教皇的决定,而是在盘算如何改变教皇的决定。
上面的“尔等”,说的就是康熙身边几个负责和西洋人打交道的奴才。多罗在北京一段时间后,康熙知道他和耶稣会神父不和,也知道自己身边的奴才都是向着北京耶稣会神父的,毕竟耶稣会神父和这些奴才有着多年的交情。所以他警告他身边的奴才不要刻意为难多罗,总在他身上找毛病。
从多罗和耶稣会神父的一些谈话可以看出,其实多罗自己并不关心中国礼仪是否真的和天主教教义有冲突。在他看来,既然教皇决定了,作为天主教神父应该做的就是服从。不管自己私下认可还是不认可教皇的观点,都不应该质疑,更不能继续争辩。在1706年2月,当得知耶稣会神父准备找康熙再签署一份解释中国礼仪的文件以后,他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警告耶稣会神父这样做只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多罗让耶稣会神父想想,罗马会不会受制于一个“异教徒”(指康熙)对天主教的解释?同时他还让耶稣会神父思考,要是把康熙牵涉进来,最后罗马做出的决定又和康熙的旨意相违背,结果会是什么?最后有麻烦的是谁?还不是在中国的神父和信徒吗?多罗劝耶稣会神父,不要陷于理论上的对错不能自拔,让他们从实际出发,去解决问题。多罗告诉耶稣会神父继续在这个礼仪问题上争辩是不值得的。他建议不要把康熙牵涉进来,给教皇施压,这样有可能把问题变得更复杂,更难解决。多罗认为最直接也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中国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按照教皇的旨意一点点修正以前的做法。按多罗的分析,如果循序渐进地在礼仪问题上做出改变,就既不会在中国教徒中引起风波,另一方面又遵守了教皇的决定。48
当然,尽管康熙作为国君不想过多掺和耶稣会神父和多罗之间的矛盾,但耶稣会神父毕竟是跟了他几十年的家奴,作为主子,有些事他又不得不管。耶稣会神父常年在康熙身边,知道康熙的脾气,他们知道把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说给康熙,康熙就会出面管这件事。大半年过去了,他们都没有办法让多罗和他们探讨中国礼仪问题。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找康熙出面。这样,他们希望能在中国礼仪问题上和罗马讨价还价。
多罗是1703年离开欧洲开始的赴华行程。离开的时候,教皇还没有最后签署禁教条约。不过多罗知道教皇要在天主教徒内部禁止中国礼仪,派他到中国就是来协调这个问题的。多罗在欧洲时就知道这个问题争议很大,也知道反对禁止中国礼仪的主要就是在华的耶稣会神父,同时他很明白自己没有学识可以和这些神父探讨中国相关的问题。当时并不是只有在中国天主教内才有礼仪问题的争论,印度南部也有类似问题,也在争论到底是否应该允许印度天主教徒继续他们的传统风俗活动。多罗在到中国之前,在印度停留了半年,就是在处理当地的礼仪问题。他还把他的各种意见发回了罗马。“6多罗深知中国的问题更复杂,更难处理。而且更现实的麻烦是,多罗发现耶稣会以外的传教士中文都很差,连一个有能力给他做好翻译的人都没有。他到中国后,选的翻译是遣使会派到中国的毕天祥神父(Ludovico Ap-piani)。毕天祥在四川传教多年。多罗用过毕天祥以后,发现他中文满文都不行,只能做最简单的日常翻译,跟康熙进行稍微深入一点儿的交流,毕天祥就跟不上了,这时多罗就必须用耶稣会的神父来做翻译。也就是说,到中国以后,在交流上,多罗连一个可信赖又有能力的翻译都没有。这也是多罗人华以后,就一直想避开谈论任何礼仪方面问题的现实原因。
辞行会见
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在教义方面有共通之处,再加上这些犹太人已经在中国几百年了,因而耶稣会神父认为他们作为第三方,写出对中国礼仪的认知,很有说服力。所以犹太人的证词会出现在耶稣会神父准备的文件包裹中。多罗接收了两位神父送来的文件包裹,也同意会看。但他始终没有做出任何批示。后来耶稣会神父还催促过几次,但都没有结果。45
1706年6月29日,康熙专门给多罗安排了辞行会见。多罗之前一直没有决定什么时候离开,当离开的日期确定后,正好是在康熙准备离京围猎之前几天。这时多罗已在北京待了半年多了。这半年中,尽管多罗和耶稣会神父在很多问题上都吵到不欢而散,但多罗和康熙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康熙对多罗也很照顾。当医生说狼的大肠能治疗多罗的肠胃病,康熙就让内务府安排在他围猎的地方捕捉一匹狼给多罗。5后来多罗还请求去汤山温泉养病,康熙也同意了。58那时候,汤山温泉是内务府皇家专用的地方。
后来康熙年间,耶稣会神父又专门去开封看犹太人的经书。可惜的是,明朝末年,一场大水淹没了整个开封,犹太人的经书在这场洪水中损失严重。后来去的耶稣会神父记录了水淹开封的往事,感叹很多古代资料可能已经遗失了。4由于有传教士持续对开封犹太人的记录,这个犹太社区在西方世界很有名。鸦片战争后,又有传教士去拜访这里,还买走了他们的古书。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普遍认为这些犹太人是回教的一个分支,因而称他们“蓝帽回回”。
跟第一次接见多罗时的安排相仿,辞行会见也是以家庭会见的形式进行的。全程没有朝廷大臣参加,只有耶稣会神父和康熙的几个儿子到场。多罗在内务府奴才的带领下从故宫西门的内务府专用通道进了宫。会见在内廷的养心殿中举行,耶稣会神父和内务府的人一起站在大殿内的西侧。在多罗和他的随从给康熙行礼时,耶稣会神父没有参与。这个细节说明耶稣会传教士这时是属于康熙一方的人。在礼仪性问候以外,康熙主要问了多罗哪天离京,以及离京以后,在中国内部的行程安排。多罗与康熙的交流一直都比较融洽,因而他在会见最后请求康熙写一封信让他带给教皇。他解释说拿着康熙的信,回到欧洲能给他长脸。康熙没有预料到多罗会在最后时刻突然提出这个请求。根据耶稣会神父记载,康熙迟疑了一下,说好吧,让他再想想。他让多罗明天再来。会见就结束了。康熙允许多罗一行去参观紫禁城内平时上下朝举行国事活动的几个大殿-由耶稣会神父带着前去。59
这对当时欧洲来说,是个重要发现。首先开封犹太人让欧洲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后,很多都因为当地的压力,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宗教,或者继续往其他地方迁徙。而在中国,他们安享了几百年的太平,和周围的汉人、回回和平相处,相安无事。而且开封犹太人里,愿意接受中国文化的,并没有受到区别对待,他们跟汉人一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艾田就是一个例子。1663年重修犹太教堂,新立的石碑上就刻有考上进士的犹太人的名字。这些开封犹太人的生活状态让欧洲看到一个巨大的希望,就是天主教也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在参观时,耶稣会神父的记录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康熙派了一个太监过来,告诉多罗明天要么到同样的地方来见康熙,要么去畅春园。太监还补充说,康熙这时还没有想到要写什么给教皇。60这个细节说明康熙到这个时候都还没有想到过礼仪之争的问题。
对于开封犹太人,他们受到世界的重视,其实源于一次误会。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一位上京赶考的名叫艾田的人,听说了传教士利玛窦的大名,怀疑利玛窦传的西方的教和他们族人奉行的教法一样,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利玛窦在与艾田的交流中(用中文交流,艾田不会希伯来文),发现他的族人继承的教法是犹太教。艾田告诉利玛窦他们已经在开封持续奉行这个教法几百年了。利玛窦立马察觉到这是一个大发现,便把这一消息传回了欧洲。利玛窦1610年去世,之后三年,负责中国教区的龙华民派艾儒略神父(Giulio Aleni,1582-1649)去回访开封的犹太人。艾儒略懂希伯来文和多种中亚地区的文字,所以会派他去鉴定开封犹太人是否真有古代传下来的经卷。艾儒略去后见到了古经卷,而且证实开封犹太社区里还有懂希伯来文的人。43
耶稣会神父的记录中有意回避了当天下午,没有说明到底康熙召见了哪些神父来商讨如何给教皇写信。但第二天多罗再次来见康熙的时候,康熙就突然提到了中国礼仪的问题。根据后来多罗所言,当天下午康熙找的是徐日升神父,但徐日升神父否认是他把康熙引人礼仪之争的。
犹太人的故土耶路撒冷地区是各大古文明的交汇地带,陆地部分处于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之间,濒临地中海,又和希腊文明相连接。公元前8世纪开始,犹太人在每一次被征服后开始流散各地。公元前330年,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后,耶路撒冷就处于希腊的势力范围之内。公元前37年,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汉代,罗马人统治耶路撒冷地区。基督教耶稣受难等很多影响世界的事件都发生在罗马人占领时期的耶路撒冷。罗马人摧毁了犹太人的教堂,把犹太人当作奴隶卖到欧洲。从此犹太人更大规模地流散到世界各地。开封犹太人教堂曾经有三块石碑(分别刻于1489年、1552年、1663年)自叙其历史,其中1552年的石碑声称“自汉代入华”大概就是对应犹太人在罗马人统治下的流散。”学者认为,汉代入华应该指的是最早到中国的犹太人,而开封犹太人,根据他们的犹太经卷以及其他材料判定,学者大多认为他们是宋代入华定居的。还有学者在《宋史》中发现“僧你尾尼等自西天来朝,称七年始达”的记录。而开封犹太人有记录的所有拉比(rabbi)的姓氏都是Levi,这和“你尾尼”的音能对上。40开封犹太人是从丝绸之路迁徙到中国的。学者根据他们留下经卷中一些字词音韵考证,证明他们与波斯犹太人有关联。“除了开封犹太人以外,中国沿海还有犹太人的痕迹。此外,因最早进入敦煌洞窟而大名鼎鼎的斯坦因,在1901年新疆一次探宝发掘中,无意中发现了唐代的纸张,而纸上的文字竟然是用希伯来文书写的波斯语。多亏斯坦因两种语言都懂,才发现了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现在已知该纸还有两页存世,一张是残存页,藏于大英图书馆;另一张完整的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些纸张说明犹太人早在唐代就到新疆地区来做生意了(纸上内容记录的就是他们在做羊的买卖)。42
第二天,康熙在畅春园接见了多罗。康熙首先对多罗说,他没有更多的东西要写给教皇了。要说的,要写的,之前都说过写过了。康熙说他只是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中国礼仪问题。康熙说中国的礼仪活动都是在儒家传统中慢慢形成的。如果天主教认为这些活动和天主教教义可以调和共存,那么这些神父就可以继续在中国传教。如果认为不调和,那么就不要再传教了。康熙还专门强调了一点,他说这些话不是在谈论二者到底调和与否,只是指出一个现实。”换句话说,康熙的意思,中国的礼仪就是这样的,你天主教觉得这教能传就传,不能传就算了。然后康熙要求多罗把他的话带给教皇。
多罗知道他没有能力说服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所以到京后并没有主动提及中国礼仪问题方面的事。这完全出乎北京传教士的意料,他们反倒很着急,希望和多罗探讨这个问题。1706年1月22日,德国神父纪理安给多罗写了一份书面提议,要求与多罗探讨礼仪问题,但多罗并没有回应。37后来,纪理安又联合法国神父雷孝思(Jean-Bap-tiste Regis)向多罗提交了书面请求,请他查看耶稣会神父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观点。他们还附送了一个文件包裹,里面包含了90份各种关于礼仪问题的文件。38这些文件都是耶稣会神父为了论证他们的观点,在1700年收集起来的。包裹中有耶稣会神父对中国礼仪的解释,有康熙当年在该解释后写的评语,有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对中国礼仪的解释,以及一份开封犹太人对中国礼仪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