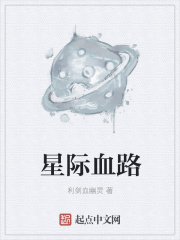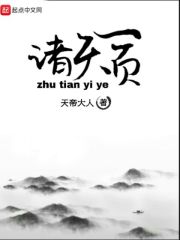第五章 教皇使团和康熙派出的洋钦差 (第2/5页)
孙立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严肃的话说完以后,多罗并没有争辩,只是连连称是。根据传教士记载,康熙这时口气稍微缓和了一些。康熙向多罗解释说,他个人倒是认为中国这些传统和天主教的教义是可以调和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在大清容留天主教的原因。多罗当时也没有想到,在这最后临时增加的会见中,康熙还是被牵扯进了礼仪问题之中。多罗当时的回答还是得体冷静的。多罗说他一个外国人,不懂中国礼仪,尽管听到过相关争论,但他自己没有资格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康熙应该也没有料到,多罗竟然会完全回避这个话题,一句答复都没有。康熙没有就此罢休,接着追问多罗,你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说说,到底中西方在什么问题的操作上是不一样的。多罗又说了一大堆话,说自己无知,谦虚了一阵,然后才说,据他所知,儒家对于儿子为父报仇,是赞同允许的;但在天主教中,无论什么情况,报仇都是不被允许的,就算是儿子为父亲报血海深仇也不被允许。62
多罗到北京以后,其实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到中国来宣布和执行教皇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即不再允许人教的信徒继续参与很多中国传统的风俗活动。作为教皇特使,多罗本以为他有权对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发号施令。按照他的预想,到了北京以后,他要把各位耶稣会神父召集到一起,在天主教内部就把礼仪问题处理了。让多罗没有预料到的是,表面谦恭的耶稣会神父,其实根本不听他的。他们利用和康熙的特殊关系来和他周旋。
康熙听到多罗举出的例子,并没有生气,反而很耐心地引经据典做了很长的解释。大约在场的耶稣会神父对儒家经典不熟悉,所以没有记录清楚到底康熙引用了哪些古籍的话来论证这个问题。他们只提到康熙做了很长的解释后,多罗连连称是。康熙也就很愉快地结束了会谈。63对于复仇这个问题,儒家和天主教各有各自赞成和反对的理由。所以多罗到底是真心认可康熙的解释,还是适可而止选择退出争论,我们无从得知。
多罗与礼仪之争
接见完毕以后,康熙的心情还是很好的,他恩准多罗一行在园中游玩,让他坐上龙舟在园中的湖里欣赏美景。康熙的第二子,也就是当时的太子,在会见结束以后,还邀请多罗到他的私家园林里去看看。多罗很开心,感觉未来的皇帝也会继续优容天主教。在去太子花园的途中,康熙派他掌管内务府的大皇子带着仆人,又拿了几套礼物过来,让多罗再选一套给教皇带回去。多罗选了一套黄色的瓷盘。“这个追加礼物的小细节,说明康熙对多罗当天的表现是满意的。
朱批:知道了。36
第二天,康熙又派人把头天说的关于礼仪问题的话,用文字形式强调了一遍,交给多罗,让他带回欧洲。康熙原话的底稿已经佚失,现在只有据传教士留下的记录把意思回译为中文。康熙写道:
康熙四十五年五月十六日,赫世亨、张常住、赵昌传宣谕旨,六月十九日,博津我跪受。恭读明主训旨,始知我之所行最为无理。前日与沙国安同行,未有谦让,与之争先。我二人虽非不睦,但我无理,有违大主圣意,铸成大错。今我竭力仰副大主训谕,嗣后不敢与沙国安争先,必谦逊和气,断不违明旨,惟叩请仁主宽恕我此大罪。为此谨奏。
五月二十日,圣上对多罗说过:昨天,你问过朕,是否还有其他未尽的事宜。朕后来想了想,也没有什么其他具体事要交代你办,就是要你把朕的一个意思带给你们教皇。在中国这里,两千年来,百姓都推崇认可孔子的说教。而从利玛窦入华算起的两百年来,特别是我在位的这四十几年,西洋人在这里没有惹出什么是非。但是如果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跟以前的成规有冲突,西洋人将很难继续在中国立足。65
博津谨奏:
从耶稣会神父的记录来看,多罗收到这份声明后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康熙也没有继续纠结中国礼仪这件事,第二天就出京打猎了。在打猎的途中,还下旨让留在宫中的奴才赫世亨去问多罗,还有没有上次进献过的巧克力和多余的西药,有的话,让他在走之前,再进献一些。66在多罗离开北京前这段时间,康熙让他的三儿子负责与多罗衔接,并让御膳房给多罗送去些好吃的。“在7月10日这天,多罗还让赫世亨转告康熙,菜味道很好,他十分感谢。68
把事情闹大了,康熙还是下旨要求白晋克制,注意言行。白晋的满文检讨书发回了北京。这封检讨还在清宫档案里,以前将检讨书从满语译为汉语的翻译可能不知道白晋和沙国安互相争权的故事,所以把白晋翻译成了博津。白晋的检讨如下:
康熙面试颜珰主教
在欧洲的思维中,所有人都可以被称为皇帝的奴仆,所以皇帝的仆人可以是个礼仪性的称谓。现在多罗终于明白了,白晋是真正在皇帝身边干事的那种仆人,因而多罗称其为“真正的仆人”。
康熙真正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礼仪之争的相关问题,是在最后一次和多罗会谈后。在会上,多罗告诉康熙,法国传教士颜珰主教正在赶来北京的路上,他是中国礼仪问题方面的专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其实多罗到北京以后,就知道耶稣会神父要问他中国礼仪问题,现在康熙也来问他,所以当知道颜珰来京的消息后,多罗如释重负,终于有人来帮他扛这个问题了。在多罗眼中,颜珰是回答耶稣会神父以及康熙疑问的最佳人选,最初禁止中国礼仪的观点就是在福建的颜珰于1690年代提出来的,后来教皇禁止中国礼仪的条约也是基于颜珰的说法。所以,站在多罗的角度来看,颜珰是世界上解释教皇禁约的最佳人选。
我不得不提醒你,那位神父是皇帝真正的仆人,因而无论怎么让着他都是对的。35
自从明代万历年间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如何把天主教引人中国就涉及各方面的具体问题。概括起来可以说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语言,二是行为。语言就是翻译,要把天主教的概念用中国的语言和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行为就是如何把天主教融入中国传统的行为方式中,同时又要保持天主教的宗教行为方式。这些总结起来很容易,但操作起来却是千头万绪。每一个具体问题,不同的传教士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引起争议。比如天主教中的神(“Deus”,也就是现在英文中的God)应该翻译成什么?这个问题就在天主教内部争论了几十年。最早传教士利玛窦决定把“神”翻译为“上帝”,但后来有些传教士又认为不对,应该翻译为“天主”。还有传教士早年认同翻译为“上帝”,后来又认为这个翻译是个错误。这个“神”的翻译就是中国礼仪之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然康熙也是这个意思,肯定了白晋才是他的人。多罗在多方了解以后,也终于明白了康熙所谓白晋是他“府内之人”这个名号的分量。他也赶紧写信给沙国安,让他不要再和白晋争了,他信中和沙国安讲:
1693年,颜珰作为福建教区主教,为了在他的教区内统一传教士的思想,结束争论,就在七个有争议的问题上做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一条就是,停止使用“上帝”,而改为使用“天主”来翻译天主教中的神;第二条是停止在教堂内挂“敬天”的牌匾;第三条指出前任教皇同意教徒参与祭孔子、祭祖的决定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第四条要传教士劝说教徒停止参与祭孔子、祭祖活动;第五条,家里要放祖先牌位的教徒,应该注意牌位上的字眼,比如牌位上的名字后如果有“神位”“灵位”的字眼,则把“灵”“神”去掉,仅保留“位”字;第六条,要求传教士不能继续在教徒中宣称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教义一致这样的论断;第七条,要传教士减少利用中国古书来讲解天主教教义。颜珰在他的福建教区发布了这七条规定以后,就把规定发回了罗马,要求罗马裁决。差不多在颜珰之前四十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在1656年已经对部分中国礼仪问题做过批示。颜珰的七条规定相当于掀起了新一轮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当时之所以存在长期争论,是因为背后有说不清楚的理论分歧。比如孔子的儒家到底算不算宗教?这在现在依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祭孔仪式中的孔子是什么角色?还有祭祖先的仪式中的祖先是什么角色?在祭祀中,孔子和祖先有“神”的性质吗?为了裁决这些理论问题,当时的教皇在罗马成立了一个四人裁定小组。对于当时的天主教来说,中国是一个新的区域,罗马处理这些教义问题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小心谨慎。为裁定相关问题,罗马的取证和各方询问的过程持续了近十年。最后的裁决报告,也显示他们做了很充分的功课。比如,他们裁定中国的祭孔和祭祖仪式中,是有“神”存在的,引用的就是孔子《论语》中的“祭神如神在”这句话。罗马的认定意见,总结起来就是中国传统的礼仪活动中有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情节在里面,不能视为单纯的世俗活动。由于天主教的教义只允许信徒心中有一个神,那么人教的信徒就不能再参与中国传统活动中有宗教情节的部分。(见附录三,颜珰关于中国礼仪布告)。
这怎么可能是个问题?怎么可能有人对白晋是我们的使节有疑问?他在我们宫中二十年,满文中文都会,一直在父皇那里效力。而谁是沙国安?谁认识他是谁?34
中国礼仪之争之所以会持续那么多年,根本原因就是问题本身存在争议,双方意见都讲得通。康熙在与颜珰会面前,专门抽时间看了颜珰的七条论断。康熙看完后,和他周围的奴才说,颜珰论述“浅薄”,但他也没有认为其中有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总体来说,康熙是愿意和颜珰会面交流的。긍
多罗似乎不完全明白派亲信出使的意味,也不明白康熙强调这个“御前”之人的意义,因而他只是把信中的措辞稍微修改了一下,实际上还是让沙国安负责带领整支队伍,并把装有礼品箱子的钥匙也交给了沙国安。但在1706年6月,当白晋和沙国安两位神父到达广州,在那里等船去欧洲的时候,二人产生了矛盾,两人开始争论到底谁才是这个使团的主导,并把问题传回了北京,要北京给出明确指示。当时管理康熙内务府的是康熙的大皇子,听到这个事情,当着众多传教士的面就发火了,说:
但让多罗等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颜珰在会见康熙时,把事情搞砸了,大大地激化了礼仪之争的矛盾。最后也影响了多罗一生的命运,令他最后都没能回到欧洲,客死在了澳门。
派身边的亲信和亲近奴才出使,是满蒙的老传统,这和汉人传统中派有身份的官员出使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康熙强调白晋是他“御前”之人这一点,而白晋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官职。
颜珰入京之前,主要在福建传教。从1681年入华算起,他在中国已经二十几年了。完全出乎康熙意料的是,见到颜珰后,康熙发现他的中文很差,基本不能交流。康熙在会面前,以为这个来华二十几年的传教士,中文水平应该和张诚、白晋神父差不多。这两个神父1689年入京时,都还完全不会中文。但学了两三年,中文满文都过关了。颜珰的中文在康熙看来不是差一点儿的问题,而是基本不会。康熙在会见中,已经照顾颜珰是外国人,放慢了语速,但即使这样,简单交流到第三个问题,颜珰就听不懂了,只好由康熙身边的耶稣会神父来翻译。当时跟在康熙身边的是巴多明神父。巴多明神父1698年入华,比颜珰晚十七年。康熙又想这位颜珰神父是不是只是口语不行,因而问他,认不认识大厅木头牌匾上的字。牌匾上写的是“华岩云阁”四字,但颜珰只认识其中的云字。1康熙彻底生气了,问颜珰:“怎么与你交流。你说也不会,写也不会。算了,现在说的你也听不懂。”72当然颜珰还是很尴尬的。对于康熙来说,这次会面让他最气愤的是,罗马方面和多罗竟然说他是中国问题专家,而且罗马对于中国礼仪问题的见解是基于颜珰的论断。
为了显示对教皇的敬意,我特地选派了我御前之人白晋。白晋是真正侍奉我左右的人,所以我选他代表我把礼物送给教皇。当然,白晋跟你们其他人一样,是个神父。但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在我身边服侍多年的人,也是我府内之人。我让他全权代表我赠送礼物给教皇。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