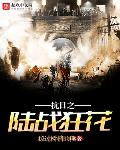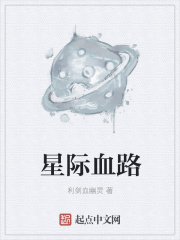第三章 学做骑手
孙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根据“美团”和“饿了么”发布的研究报告,两个平台分别有77%和75%的外卖骑手来自农民工群体。这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同时它也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平台劳动虽然是新职业,但是参与其中的依旧是耳熟能详的“旧人群”。而恰恰是这样的“旧人群”,他们的职业伦理出现了“新变化”,才更值得我们注意。对于离开农村的农民工来说,城乡的差异和平台的分化管理加剧了他们个体化、原子化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在外打拼成为一种习惯。那么,他们真的只是原子化的人吗?答案是否定的,也是复杂的。因为他们不但未能成为个体化的自由人,反而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吉登斯在讨论现代性与现代社会时,提出了“自反现代性”的概念。他认为,个体不断地自我反思、调试自身实践并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是现代人的重要特征。这样的阐释放在投身外卖的劳动者身上十分适用。中国当代劳动者的职业伦理正在发生显著变化。面对加速变化的社会,工作不再是为了稳定和长期收益,而是更趋向于追寻短期劳动利益的最大化。据我的观察,从事外卖的劳动者虽然也有犹豫和纠结,但会主动消解传统社会捆绑在自己身上的诸多束缚,他们会与传统认知进行协商,并在合适的时候果断脱离,积极投入到零工经济的平台劳动市场中。工作的流动性、可变性和不稳定性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曾经阐释了“制度化个人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晚近现代性中的个人看似越来越自由,但实际上并不是无拘无束的个体,而是与各种社会结构、网络、规则、制度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想,外卖骑手也正在上演此种“制度化个人主义”。他们逃离工厂,追逐“自由”,但却在“学做骑手”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深刻地与系统、平台、消费者等各种元素绑在一起,而在此过程中,他成为首要且唯一的责任人。在外卖的江湖里,获得收入、学习话术、忍受污名、打架反抗等均成了个人需要独立面对的事情。学做骑手,既是一个被平台服务规训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接受个人主义的过程。
从学理的角度分析,“学做骑手”的过程彰显着中国农民工群体甚至是更广泛的数字中下层人群的工作伦理变迁。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零工人群,并不想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在工厂或工地工作,乖乖地服从工厂、企业的管理支配。他们不想“被人管”,他们“更喜欢自由”。“追逐自由”正在成为当下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虽然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现在的工作到底是更自由还是更受限。相较于稳定、省心、离家近等更讨自己父辈喜欢的就业方式,中国二代、三代农民工似乎更加在意自己的选择和自我的感受。
外卖劳动的工作形态成为塑造骑手身份认知以及自我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骑手劳动伴随着平台不断细化的劳动组织形态和彼此竞争的机制而变得越来越缺乏联结性。它变得个人化、变得难以联结和分享。平台劳动者似乎丧失了工友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个体化的沉默与零星碎片的表达。超长的劳动时间和按件计价的薪资规则让越来越多的人沉迷其中,患得患失、囿于比较。内在的关注远远大于外在的联结。我逐渐领悟到,这群逃离工厂、远离老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劳动者加入外卖行业,折射出了中国信息化和平台化带给个人的巨大冲击。当越来越多的骑手专注于比较彼此间的收入而非共同利益时,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便形成了。在追逐自由、“用脚投票”的高速流动中,他们的数字劳动旅程就此开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成为骑手,既是一个适应平台组织管理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身份协商的过程。骑手是一份服务业工作,这也意味着个体的规训和服从不可避免。正如《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作者胡安焉所言,干快递时,“自尊心的确是一种妨碍”。在某种程度上,快递员、骑手这样的职业具有相通性。在这一章中,我将重点描述外卖骑手如何进入外卖行业、学习服务,并最终在平台上形成一种黏性劳动的趋势。我试图在分析田野数据的基础上给出一些关于数字劳动的理论反思,如为何当代年轻人会选择成为外卖骑手,在成为外卖骑手的过程中,他们对于自己身份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