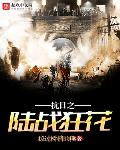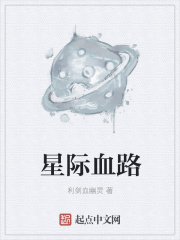视角与结构
孙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时常抵抗一种压力,那就是把外卖骑手苦情化、扁平化的压力。或者说我在抵抗一种高估性,即对于劳动人群的过度赞美。这往往是很多媒体书写期望呈现的。并不是说骑手不值得赞美,而是这么做让我无法看到对劳动或者劳动者真正的尊重与敬畏。我更希望以平视的姿态看到他们的生活,这是一群特色鲜明而又头脑灵活的劳动者,正如斯坦丁所言,“单纯从苦难的角度来看待朝不保夕者是不对的。很多人沦为朝不保夕者,是因为不喜欢工业社会和20 世纪的劳工主义,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参与外卖骑手的田野观察时常让我困惑,为什么技术的进步没有让“劳动变得轻松愉快,反而让劳动变得更加繁重艰辛”?为什么平台经济如此精细的组织和管理没有减少参与者的劳动时间,反而让他们“黏在平台上”?为什么看上去相当不错的收入无法留住骑手,反而加速了他们的职业流动?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贯穿着我的行文过程。
在书写的过程中,我时常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外卖骑手所创造的意义?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非要有一个答案,我想那应该是他们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如何抓住机会、塑造生活的经验与勇气。无论是翻天覆地的平台经济,还是难以预测的经济政策,对于个体而言都是自上而下、被动接受的过程。这些过程往往没有真正的主体责任者,它们多被包装成国家、政府的治理型机器。这也就意味着谈论意义本身十分困难。但是,底层数字劳动者的言语、实践却与此全然不同。他们显眼、明亮、直白,虽有时略带粗鲁或显得不合时宜,却完全不影响他们是真正的主体行动者这一事实。本书想展示骑手在日常生活、劳动中“反转结构性压迫”的一些瞬间和故事。骑手们在诸多困难和不平等面前积极地对抗,来为自己争取更自由、更体面的生活,那些谋求快乐与自由的小策略、小技巧时常让我无比感慨。他们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社会重组、关系重建等宏大命题同时存在,他们积极参与其中,徜徉其中,努力且坚定地成为社会变迁、经济变革的一部分。传统的劳动关系被销蚀,平台经济所塑造的新的关系在酝酿,新的可能和新的束缚在同时产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看到大规模数字化、城镇化、平台化所催生的新型能动力量。这些能动力量来自数字劳动者。
在这个研究中,我努力地让自己舍去一些宏观、漂亮的“外衣”,去关注个体劳动者鲜活、热烈的劳动和生命体验。我努力不去把他们框在一个成形的理论框架中,不去“削足适履”,希望鲜活的经验材料能够引导我慢慢看到一幅模糊却令人欣喜的劳动生态图谱。
全书共有八部分,围绕“过渡劳动”的概念来阐释外卖骑手这一人群的劳动与生活实践。主体部分安排如下:
最后,与所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相似,本书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用个体鲜活的生命经验连通时代变化与社会发展的脉搏,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数字劳动与平台劳动的研究越来越变成一个宏大而丰富的概念框架,这就意味着穷尽其意义和进行总体性的论断变得越来越困难。当下诸多关于数字劳动或平台劳动的研究以非常翔实和重要的数据剖析了数字化在管理和控制层面的种种可能,但这也让我隐隐感到忧虑,如果所有结论都指向控制性本身,那么想象与讨论主体性的可能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又在哪里?二元的框架让我有些害怕关于数字劳动的丰富性、趣味性、立体性会被抹杀。保罗·威利斯说,“批判性民族志的研究实践为理解人类所展示的这幅历史巨卷提供了能动性”,对此我深以为意。因此,本书在论述中无意去迎合、强化主流的常识性问题,也不想简单地批判“资本万恶”。同时本书并不希望“理论先行”,或者将丰富有趣的在地材料硬塞进“社会理论的紧箍咒”。相反,我想大胆一点,用书写的开放性去看到一个生动的、自主涌现的社会动态,一个复杂流动的脉络图谱。
第一章主要讲述平台的组织化问题,即外卖骑手是如何被超强的平台组织聚合在一起的。在剧烈而快速的变迁中,骑手的劳动状况正在面临一种矛盾的拉扯:一端是平台的组织化不断增强,另一端是劳动的灵活性不断增强。“出入自由”成为该职业的重要特征,也同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朝不保夕者”,而流动与奔波成为其必然选择。
在田野中,我的注意力往往只能集中在一种情境上面,当多种情境同时出现在眼前并相互交织、不断变动时,我作为研究者的角色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退出与参与的选择性也在不断地增多,这使我感受到了一种复杂感。它时而让我兴奋,时而让我沮丧。在行文中,我将努力呈现一些复杂感,与此同时,也不得不去“悬置”更多疑问、焦虑和不确定。我想,这大概正是田野调查的魅力所在。
第二章讲述了平台技术体系的生成,以及它如何管理骑手、如何与骑手互动。借由算法的智能性,平台建构了一种“生成性管理”的模式。于是在人-机没有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出现了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情况,因为作为“人”这一端的骑手面临诸多无法摆脱和解决的困境。
其次,本书希望在个体生命整体性的观感之上,关注其劳动与生活的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情境化关注“此情此景”,这对日新月异的平台化劳动来说十分重要。昨天发生的事情可能在今天不会重复,思考当时的情境与现在的关联就显得尤为重要。丁未在《流动的家园》一书中曾讲述过其“情境化研究”的方式,而个体劳动者的所思所想确像一条条充满经验的河流。这种经验的河流彼此并行,却又相互交融、激荡,而周边环境的变化也会或轻微或剧烈地改变河流的流通情况。“情境化”的另一种理解是“脉络”,这更像是一种联结的思路,在看到“此情此景”的同时可以联系到“他情他景”,甚至是更广阔语境下的现实对比。
第三章回到作为劳动者的整体性视角,讲述了劳动者成为骑手的过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劳动者进入外卖行业,折射出了信息化和平台化带给个人的巨大冲击和虹吸效应。当越来越多的骑手专注于比较彼此间的收入而非共同利益时,制度化的个人主义便形成了。这也是过渡劳动形成的前提条件。
关于本书的视角,首先,我希望专注于劳动者个体生命的整体性。本书采用一种韦伯式的研究方法,先了解研究对象的生命世界,再利用学术概念进行阐释。在关于外卖骑手的描述中,本书希望看见关于骑手立体的生活“构型”,这里的“构型”不仅涉及他们的劳动状态和工作轨迹,也涉及他们的生活、家庭、交友、思考等。它们交杂在一起,而我无意将其分开,也无法将其分开。外卖骑手的“过渡劳动”体现在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许多地方可能显得细碎、重复,甚至无聊,但对于本书的分析来说,它们构成了劳动意义和生活本身。虽然书中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与骑手的劳动生产相关,但我仍希望自己能够跳脱“生产”框架,用“整体化的方法”去关注人、劳动和流动的问题,并以此去理解社会的、空间的、性别的现代化社会场域和社会关系。
第四章和第五章关注外卖劳动的两个重要面向:区隔感与性别化。第四章试图阐释外卖劳动在何种程度上变成一项“区隔劳动”,以及此种“区隔劳动”如何在身体、流动、监管等不同层面加剧了外卖骑手的劳动过渡性,包括风险区隔、时空区隔、流动区隔。在此过程中,外卖骑手明显感受到了疏离和区隔,这令他们没有归属感。第五章讲述了性别劳动,即女性如何利用这份工作谋求短期利益。受传统家庭分工的影响,女骑手似乎更加知晓并了解外卖作为一种“生活缓冲”的重要作用,她们在生活、家庭遇到困难之余投身外卖,并力图借助外卖劳动来度过困境。同时,由于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再生产劳动,过渡性也体现在她们需要兼顾母职和工作上。
如前文所言,本书想要论述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外卖劳动如何变成一种过渡劳动?在我们对于“工作”的诸多定义中,“稳定”成为其中的重要特质。几乎人人都希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体面而稳定,这不难理解,因为稳定的工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个体在多变、危险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在风险社会下,稳定的工作就像一间“避难屋”,成为个体安全感和成就感的一部分。而对外卖骑手这样的群体来说,稳定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本书希望看见并分析造成这些不可能的原因与机制。
第六章主要关注骑手劳动的主体性问题。本章围绕“数字韧性”这一概念的提出进行阐释——“数字韧性”是一个涵盖了外卖员劳动、生活与社会关系的动态框架,它关注能动性发挥的日常氛围和具体情境,也关注数字技术和流动性给这个群体带来的能动性方面的新变化。本章没有将描述的范围圈定在罢工、抗议这样的直接对抗与冲突中,而是希望包括更广泛的能够彰显数字劳动者主体性的实践与活动,如对“过渡性”的利用、“逆算法”的劳动策略、媒介社群的建立和使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