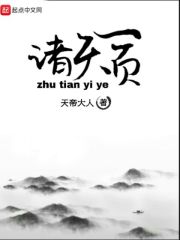何以为家 (第2/5页)
孙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我说你赶快走吧,赶快走。他不走,说,哥,我就喜欢你这款式的。我靠!你说怎么弄,我说你赶快走。我跟你说,我直接崩溃了,就那种刺激……后来他走了,离开200米左右的时候,我还给拍了个视频,就是背影离开的那种。我怕回头万一需要证据。后面的时候,我就没敢睡,不敢睡,听到有人走过去我噌地就坐起来。一直挨到凌晨四点多,实在扛不住了,睡了两个小时。六点卖菜的商贩经过,我就醒了。
我使劲儿说他。我说:“爸爸给你钱,是为了让你好好吃饭。我还特地给粉店的老板交代,多给你加点肉。我怕你吃不饱。……爸爸在北京打工很辛苦,你也知道,你这样,我很生气。人要讲理,不能撒谎。你撒谎骗我,这样好吗?”他也不吭声,后来就说:“好,我知道了,以后不了。”儿子还是有些怕我,他听进去了。
第二天,吴之峰立马联系了妹妹,要了一个帐篷。之后的露营,他都睡在帐篷里。“拉上拉链,就没有人敢轻易动我了”。又过了几天,吴之峰的同事说另外一个闪送员的小区也封闭了,他没法回家。吴之峰听到了,觉得应该帮他。吴之峰与那个闪送员加了微信,两人一起搭伴过夜。这样吴之峰的心里也踏实一些。吴之峰从小在外打工,随遇而安是早已养成的本事。虽然经历了被骚扰的惊险,但是这仍旧没有打消他在外露营的想法。最长的一次,他有四个月在外露营过夜,用他的话说,就是“四个月没见过屋顶”。
张文友的大儿子上六年级,与后妈一起生活,难免叛逆。张文友在外务工,觉得愧对大儿子。为了减少母子间的摩擦,张文友在学校附近餐馆给儿子订了午饭,放学后他可以过去吃饭,不用回家。张文友还给儿子买了儿童手表,保证儿子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大儿子隔三差五就跟张文友要零花钱买些瓜子糖果之类的,张文友也不过问,一般都会给钱。有一次,儿子打来电话,告诉张文友自己在米粉店吃了11块钱的粉,让他付钱。他加了米粉店老板的微信,转给老板11块钱。后来打电话过去,老板告诉张文友,他儿子只吃了3块钱的粉,把剩下的8块钱“套现”拿走买零食了。这让张文友十分生气。
我在2022年 5月的时候找他吃饭,那段日子他正好“露宿街头”。我们聊天,他热情地向我传授野地住宿的注意事项和经验。他在五金店买了一个便携卡式炉和一口小锅,每天给自己做两顿饭。他计算好了每顿饭需要的火候,两顿饭一小罐燃气正好够。大部分时候,吴之峰给自己煮面、煮粉,有时候,他会做一些拌面就着辣椒酱吃。他笑着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一天傍晚,他给我发来一段微信视频,视频中他把车停在一片建筑工地的外围,周边七七八八长着野草,他在露出的黄土地上铺开瑜伽垫,用卡式炉烧水,煮了一些燕麦和螺蛳粉,并配音说“这个搭配味道好极了”。
张文友挂念着老家的亲人。父母年纪大了,和两个儿子住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因为与当地政府谈不妥搬迁费用,他们没有搬下山,如今变成了村里唯一一户住在山里的人家。“下暴雨的时候,山体会动,安在我们家旁边的山体地动仪会响,房子已经裂开了一个大口子。真害怕哪一天,山体滑坡,连着我们的房子全部推下去,就完了。”聊天的时候,我和学生们给他出主意,让他拨打当地政府的市长热线,他摸摸后脑勺,为难地说“回头试试吧”。
除了吴之峰,我也听说过其他骑手“露宿街头”的精彩故事。他们普遍对“睡大街”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好感甚至赞许。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苦难,恰恰相反,他们会怀念一起在公园的长凳上躺着聊天的时刻,会时常想起黑夜里的寂静和天上闪亮的星星。还有的骑手会在深夜等单无聊的时候,跑去旁边郊外的河边钓鱼。他说,一天的吵闹可以通过钓鱼时的安静被消化,自己也可以有个喘气的机会。
省了钱,可以给儿子交学费。之前在县城买了房,还有房贷。今年7月份回家,我又贷了10万装修贷。一个月加起来要还5000多吧。压力不小的。但是我真的感谢这个众包。北京的单子真的多。别看骑手是最底层的服务业,挣得不少。现在还完了贷款,还能剩下一两千。
吴之峰和其他骑手“露宿街头”或者寻找安静时刻的故事道出了许多外卖骑手在疫情期间的共同经历,他们一方面受到空间上的管束,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地创造属于自己的、不被管控的空间,尽管这样的空间有时会充满危险和不确定。我时常在晚间写作的时候禁不住想,此时吴之峰和他的骑手朋友,不知道又睡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聊什么,又在担忧什么。很明显,骑手诸如此类的空间流动并不符合主流意义上城镇化的要求,它也很少与城市中的居民发生交互。骑手的露营之地多是地下通道、天桥走廊、工地或者市郊荒地等少有人驻足的地方,他们不希望被打扰,也不希望被管理。这样的区隔,与其说是被动形塑的结果,倒不如说是骑手主动创造空间的过程。这既是一种谋求生计的探险,也是生命历程中丰富自我的体验。
几经周折,张文友在孟天河的介绍下开始跑美团众包,并在小武基村河东侧租了一个小单间,月租530元。其中租金500元,网费30元。他对于自己的小单间十分满意,主要是因为便宜。的确,这应该算城中村里最便宜的房租了。“大概只有两三平米的样子。一张单人床,一个小衣柜,够了。”张文友笑着说。我几次提出想去看看他的房间,他显得十分不好意思,说“没啥可看的”。房间里外都没有厨卫。平日张文友使用村里的公共厕所;想要洗澡的话,就去桥对面的一家澡堂,洗一次8元。遇上夏天出汗多、洗得勤,张文友舍不得花钱,有时就会找个脸盆在屋子里擦擦身,隔几天再去澡堂。
上海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