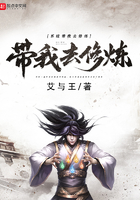“学习”服务 (第3/5页)
孙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当骑手抛弃平台话术、用自己的方式与顾客打交道时,他们才发现不同人群间总是存在“交流的无奈”。乍一转入外卖行业,这些粗犷的汉子对于情感劳动细致入微的表现方式无所适从。他们被卡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办时,逐渐在与人交流中慢慢地意识到需要从头学习如何“服务别人”。对于适应了高强度劳动的农民工来说,学习精细化的服务流程并不容易。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平台经济对于整个社会的冲击不仅仅体现在生产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和文化关系层面。进入服务业的农民工群体被迫放弃基于传统亲缘关系、差序格局的社会联结,转而接受基于专业主义、理性化的工作伦理。原有的邻里关系中包含着熟悉、信任和包容,但是这些内嵌在乡村关系下的伦理一旦遇上市场交易与服务专业化,便失去了它的立足根基。他们需要换上一套新的交流准则和交流技巧,学会联结陌生网络并获取短期信任。
接下来讲述的两个故事,比挨骂再升一级,都跟肢体冲突有关。通过这两个故事,我想描述一种看似特别、但在骑手看来又十分普通的境况,那就是如何在“学习”服务别人的过程中进行反抗。这些选择“反抗”的骑手大多年轻气盛,对于劳动的尊严或者“面子”十分重视。如果有人触及这些底线,他们会毫无顾忌地把平台灌输给自己的“服务理念”抛诸脑后,并为了自己的尊严而战。这种情况并非寥寥无几,而是比比皆是。
虽然情感劳动在外卖行业中的要求和表现并不如航空、家政、按摩等行业那么明显,但它的确是与顾客沟通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礼貌、友好、有耐心的服务态度更加受到平台和消费者的鼓励。平台推出的服务话术,旨在形塑和鼓励外卖行业的“情感劳动”准则,但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这些话术并未被骑手接受。驴哥和周边的队友们都戏称自己是“大老粗”,觉得平台给的话术“太矫情”,他们说不出口。例如,送餐结束后,平台会要求骑手主动感谢顾客订购平台餐品并邀请顾客给出好评。获得“五星好评”的骑手会有积分奖励。但实际情况是,多数外卖员从来不会对顾客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觉得“不太好意思”,对此“没办法开口”。
虽然骑手被平台、站点、算法的层层管理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老老实实、言听计从。我在田野里遇到的骑手大多十分洒脱自信,深知平台管理留有的诸多协商空间。用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话来说,他们在一些时刻展现了工人该有的聪明和坚持。“打架”这种事情在服务业十分不被看好,因为它不但意味着买卖生意的完全丧失,更预示着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就此“结仇”,老死不相往来。可恰恰是这样一种极度不被看好、不被鼓励的事情,却屡屡出现在外卖骑手的身上。对此我很好奇。外卖骑手为什么要跟别人打架?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争吵或者打架,对于骑手而言具有什么样的用意和目的?
我能够想象,一个在写字楼安静环境中工作的白领突然接到驴哥的电话,大声嚷着让其到楼下取餐时的情景。顾客可能被吓了一跳,也会觉得驴哥的语气不够友好。一个差评,骑手被罚20元到50元不等,相当于5单到8单所赚取的收入。话语表达与交流问题成为很多骑手得差评的原因,他们不理解却也无可奈何。
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的研究中曾经剖析过工人群体的主体性问题。他认为,工人子弟的主体性往往不会自我标榜,而是隐藏于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瞬间。例如,他们反对学校文化,过早辍学,不喜欢主流的教育模式。这些在广大社会群体中被视为“正途的”、合适的教育逻辑并不能打动他们,他们喜欢“逆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反智”和对学校教育的不理会,恰恰是其主体性的展现。如威利斯所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新型社会能动者,不会自诩为新型的社会主体,也不会在自己的前额贴上自制的标签。通常,人们只会借助于对他们卑下地位的侮辱性刻板印象来认识他们。不要错过下层群体创造意义的瞬间,这些瞬间在理论上无法避免,却通常未被人注意”。这样的观点和逻辑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骑手打架的问题。
什么叫态度不好?说话声音大就是态度不好吗?我身上挂着6个单,在路上拼命跑!我没觉得自己态度不好。我就是让他下来取餐!这也错了吗?
第一个故事来自赵武,我们前面提起过他。他来自东北,幽默善言,是美团众包的一名骑手。2020年8月,他与一小区保安因为进出的问题争吵起来,并闹到了派出所。以下是他的自述:
驴哥瞧不上平台的服务话术,这也让他吃到了苦头。在刚开始干外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驴哥收到了三个差评。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如果差评继续增多,驴哥将面临被封号的危险。驴哥不服气,一直给客服打电话申诉,但始终没有成功,客服表示有录音为证。他给我看手机后台的差评留言,其中一个给差评的顾客说他“说话声音太大,态度不好”。对此,驴哥有些恼怒:
有一次,我去送餐,在中国电商(建筑物)。门是开着的,我就往里进。保安让我出来,不让我进。我出来后,他把门关上,说不是不让你进,你得走着进,不能骑车。我就走着进去了。但我出来之后,发现有人从他旁边骑车进去了,他不管不问,把门打开。我就特别生气,跟他理论了几句。这保安挺霸道的,一顿骂我,还说要打我。我说你来打,我就把头伸过去了,然后他就推了我一把。他其实没打我,推了我一把,我就躺地下了。
可在实际跑单的过程中,无论是众包还是专送骑手,对于平台的话术要求都有些不以为意。驴哥是北京良乡楸树街的众包骑手,可能是因为他长得黑、脸略长、嗓门大,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黑驴”。后来,这个绰号越传越广,大家都喊他“驴哥”。说到平台的服务话术,驴哥并不在意,他说:“没啥用处。说过来说过去,顾客见你就几秒钟的事,哪能啰嗦过来啰嗦过去?谁听!”我问驴哥如果不用平台的话语该怎么办,他没有详细地解释,只说按照自己的想法,说上几句,“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不能随随便便让他。本身就挺憋屈。他看我不起来,说了一些狠话,说我垃圾还是什么,还说要来点黑社会那个性质的给我看看。我说你随便,你怎么着都行。我不在乎。他就是吓唬人,碰着胆子小的可能就被吓唬住了。但我这么多年了,啥事没遇到?我不在乎。
当然,不同的工种和站点对于服务话术的使用要求存在差异。例如,关于众包骑手对服务话术使用的检查较为松散,多数情况下无人监管,而对专送的要求则更高,站点和平台会通过顾客的后台反馈、线上问卷或者通话录音来检测骑手是否使用了标准话术以及是否“话语得当”。
报了警,派出所出来调解,让他给我赔礼道歉。刚开始他不赔礼,我说你不赔礼咱就耗着,反正今天钱我也不挣了。不行的话到时候就拘留你。判可能判不了,但是拘留五天一周的应该是没问题。你毕竟伸手了,有监控看着。
根据送餐的流程,外卖的服务话术被划分为很多类别,如取餐、催单、迟到、出错等。平台几乎预估了送单过程中出现的每一种情况并准备了相对应的话术反馈。服务话语中最经常用到的是礼貌用语,如“您好”“谢谢”“对不起”等。通过打造这样一套服务话术,平台希望“大老粗”的骑手可以立即上手使用,从而更好地提供送餐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