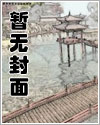第〇章 来见见社会语言学家吧:酷飒的女性主义者们在聊什么? (第1/5页)
阿曼达·蒙特尔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性别先行的思维也印刻在庞大的针对女性的性化词汇中,比如“ho”(妓女)、“tramp”(淫妇)、“skank”(粗鄙丑女,心机婊)——详见第一章的内容——而这些词全都没有与之对应的男性版本。即便是那些褒义的强性别倾向的语言也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只需想想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基于性别的夸赞就知道了。“对小男孩的赞美通常是‘smart’(伶俐)、‘clever’(聪明)这样的词,”卡梅伦说道,“而对小女孩,人们大多会夸她们‘pretty’(漂亮)、‘cute’(可爱)。”这种模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我甚至发现自己在夸我的两只猫时也说了同样的话:“good boy”(好小伙)和“pretty girl”(漂亮姑娘)。这种用词差异往往会影响孩子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且会持续许多年——当然,这样叫猫大概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影响。
另一个类似的情况是,“man”这个词出现在我们认为属于女孩的词之前:“manbun”(男士发髻)、“manbag”(男士手袋)、“guyliner”(男士眼线笔)⁺。这些词朗朗上口,但它们本质上所强调的观点是:化妆品和手袋等物品是女性专用的,因此让人觉得轻佻无用,如果商家希望吸引男性使用这些产品——而不是让它们在仓库吃灰——就必须以一种具有男子气概的方式重新包装它们。同理,像“mompreneur”(“妈妈”企业家):“SHE-EO”(女CEO)和“girlboss”(女强人)这样的词表明,“entrepreneur”(企业家)和CEO实际上不是性别中立的词,而是被默认为“男性”的。这类词的存在也说明,当一名女性在商界努力奋斗时,我们会忍不住使她们的头衔听上去更娇媚可爱。“mompreneur”似乎象征着闪闪发光的女性力量,它当然也是社交媒体上很好用的一个话题标签,但在实践中,像这样的词语非但不能消除语言中隐含的性别歧视,反而强化了歧视。
显而易见,性别偏见一直存在于语言中,但直到现在,英语文化才意识到应该进行语言革命了,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翔实语言数据,以及我们对于探究以下问题产生了空前的情感动力:我们谈论性别时有什么具体的不同之处?我们在感知男性、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的言语时又有什么显著差异?
以上现象的核心是一种普遍假设,即许多受人尊敬的职业从业者——外科医生”、科学家、律师、作家、演员(甚至是非人类演员)——都是男性,除非另作证明。这种先入为主的微妙偏见,就反映在“女医生”或“女科学家”这类称呼上,暗示着这些职位天生就是男性的,而“模特”“护士”“卖淫者”则默认都是女性。
物理学和地质学研究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与之相比,对语言和性别的研究是全新的,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关于该主题根本没有任何论着和实验数据。这一研究领域的兴起恰逢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当时在政治上亟须理解英语中隐藏的性别歧视。那时,几乎社会语言学领域里的所有人,都想谈谈人们每天是如何使用语言来创造和反映他们的性别的。这些问题之前从来没有被正式分析过,而语言学家们在过去的研究中也犯了很多错误,因此学者们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主流文化逐渐认为女性的权利问题不再具有紧迫性,许多研究也随之被淡化——尽管女性主义理论研究在学术界不再流行、但幸运的是仍然有许多少数族裔学者在该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她在1989年提出了“交叉性””的概念——总的来说、语言和性别的研究受到了阻碍,停滞不前。
偏见在语言中的表现方式极其隐秘,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语言还有文化会默认将男性视为普适的人类。这种思维在我们随后要探讨的无数语境中都有所体现,现在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大部分时候,“man”(男人)和“person”(人)在英语中是同义词。“例如,如果有人以‘I saw this person the other day…’(我前几天见过这个人)作为故事的开头,那么听故事的人通常会把这个没有修饰语的‘person’理解为一个……中产阶级白人男性,直到下文明确标示并非如此。”匹兹堡大学研究语言和男性气质的学者斯科特·基斯林(Scott Kiesling)如是说,“男性所使用的语言通常也是用于评判其他群体语言的无形对照标准。”
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随着对性别谱系和性别平等的兴趣重新涌入我们的头脑,普通人和语言学家才再次提出如下问题:一个男律师在法庭上叫他的女同事“亲爱的”算是性骚扰吗?“slut”这个词可以去污名化地使用吗?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地道歉吗?假如的确是这样,那这是件坏事吗?
我问牛津大学的女性主义语言学家、我心中的偶像德博拉·卡梅伦,英语到底是如何变得如此充满性别歧视的,它原本就是这样的吗?幸运的是,卡梅伦认为英语的DNA(元音和辅音)中并不包含性别偏见,但英语的惯常使用方式“表达(并再生产)了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的假设”。这意味着,好消息是英语对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并没有“天生”的偏见;但坏消息是,英语的使用者集体同意以一种强化现有性别偏见的方式使用它,而这种方式往往是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
讲英语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得到这些答案,这给了语言学家新的机会来收集数据,并纠正许多人仍然抱有的关于“男性和女性如何使用语言”的错误看法。是时候让他们的研究超越教室和学术期刊的限制,走向我们的会议室、早午餐桌和议员的办公桌了,因为这些发现能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运动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一直并将继续被用来反映和强化权力结构和社会规范。因为老白男统治我们的文化太久了,而语言又是创造文化和进行交流的媒介,所以是时候在这些事情上发起挑战了:我们如何与为何以现有的方式使用语言?以及我们使用这些语言的本意是什么?也就是要质疑一下我们每天所说的话,以及我们说这些话的语境,因为如果不假思索、下意识地使用一些简单的词,比如称呼语或脏话,很可能就是在强化一个我们本身并不认同的权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