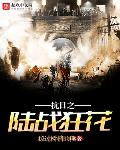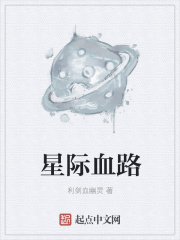易中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正面的解释是第四种,上德若谷。这是老子在第四十一章讲的。谷,就是山谷、峡谷、溪谷。前面说过,这是老子最喜欢、最推崇的。它的特点,一是卑下,二是虚空,三是包容。因此,所谓“上德若谷”,就是说,达到最高道德境界的人,一定谦恭卑下,兼收并蓄,虚怀若谷。实际上,“虚怀若谷”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这样看,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其本意就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应该像山谷一样放低身段、敞开胸怀”了。因为按照老子的说法,做诸侯,当天子,是要“受国之垢”“受国不祥”的。不能“受国之垢”,就不能做诸侯;不能“受国不祥”,就不能当天子。谁能“受国之垢”?孤家寡人。谁能“受国不祥”?不善之人。天子、诸侯自称孤、寡、不榖,不是名正言顺吗?
这三种解释,原理不同,意思一样。就是说,天子、诸侯为了得到最高的荣誉、最高的尊荣,故意“称孤道寡”,把自己说成是“不善之人”。其实,他是要当“圣上”,而且还要“独享”。否则,怎么不准别人这样自称?难怪赵朴初先生说,尊贵是王侯,偏偏称孤寡,你说这是谦虚还是自夸?这是反面的解释。
看来,这“黑锅”,天子、诸侯是非背不可的。不背,就不能“若谷”。这“垃圾箱、回收站、污水厂”,他们也非做不可。不做,也不能“若谷”。实际上,江河湖海了不起的地方,还不仅仅在卑下和虚空,更在于包容,尤其是能够包容污泥浊水、枯枝败叶,可以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同样,最伟大、最崇高的人,也一定能够包容一切,尤其是能够包容“最不能容于天下之人”。因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如果只能包容谦谦君子,不能包容卑鄙小人,那就不叫“包容”了。再说了,君子,还需要包容吗?
第三,损之而益。这是老子在第四十二章所讲,全文是“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也是解释“人之所恶,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为称”的。意思也很清楚:减损就会增加,增加就会减损。减损得多,增加也多;增加得少,减损也少。减损和增加,是成正比的。因此,为了增加,就得减损。为了“加到最多”,就得“减到最少”。是啊,既然“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那么,天下皆知其“丑”呢?岂不就是“美”?
我想,这应该是《老子》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但我不主张把这个观点,表述为“包容一切”。如果“包容一切”,那么请问,包不包容“不包容”?我是做不到的,江河也做不到。不信你把江河堵起来,看看会怎么样?对不起,发洪水了。
其实,不但至誉无誉,至毁也无毁。记得鲁迅先生就说过,要诋毁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躲在人群里,指指点点,欲言又止,然后大摇其头。这样,大家就不知道这个人有多坏。实际上,这个人可能一点都不坏。但“无毁”的杀伤力,却很大。因为如果你把这个人的“罪状”都一条一条数出来,可能就会有人说“这不是事实呀”,或者说“这也没什么呀”,甚至说“我看很好呀”,等等。如果你只是摇着脑袋说“他呀,他呀”,就至少让人起疑。疑心生暗鬼。这个本来真没什么的人,没准从此就“有什么”了。这就是“无”的力量。
看来,老子这个“正言若反”,背后可能有大文章。有没有呢?有。在哪里?在第四十章,是这样说的——
庄子说的“至誉无誉”则不同。它的意思,不是“不赞美”,而是“无需赞美”。因为根本就用不着,也赞美不了。比如天地日月,你怎么赞美?也只能说好大呀!好美呀!好辉煌呀!好明亮呀!等于没说。再说了,天地日月,需要我们赞美吗?不需要。不需要,才是最高的赞美。所以,“至誉无誉”虽未必是《老子》原文,却符合老子的思想。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第二,至誉无誉。这也是老子在第三十九章讲的,不过只有一种版本这么说,据说还是根据《庄子·至乐》改的。其他版本,文字不同。一种叫“致数与无与”,一种叫“至誉无誉”。致,就是招致;与,就是给予。按照老子的辩证法,给个不停,等于没给;要个没完,等于没要;反复赞美,等于没赞美。因此,最好的赞美,就是不赞美。就像武则天,干脆给自己立一块“无字碑”。这,大约可以算是“至誉无誉”。
反,有两个意思,一是“相反”,二是“返回”。相反,则相成;相成,则转化;转化,则返回。比方说,“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这就要“唱反调而居弱势”。唱反调,就是道的运动(反者道之动);居弱势,就是道的运用(弱者道之用)。所以,人,就应该往低处走,往坏处想。往低处走,结果是最高;往坏处想,结果是最好。如果还能“受国不祥”,那你就是“天下之王”。这就是老子的基本观点:最柔弱的最坚强,最卑下的最崇高,最虚空的最实在,最原始的最先进。这也就是老子的思想方法:反过来想,反过来说,反过来做,反过来看问题。总之,反着来,就对;反着来,就行;反着来,就能无往而不胜。
第一,以贱为本。这是老子在第三十九章讲的。老子说,尊贵,是以卑贱为根本(贵以贱为本);崇高,是以卑下为基础的(高以下为基)。所以,天子、诸侯,才用恶名来称呼自己(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榖)。这倒是很符合老子的思想方法:相反相成,物极必反。相反相成,则尊贵从卑贱中产生。物极必反,则卑贱到极点,就是尊贵到极点;卑下到极点,就是崇高到极点。所以,天子、诸侯,得把“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
当然,也只有反着来,才能“大”。因为“道”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反”。《老子》第二十五章就说,如果一定给“道”命名,也只能勉勉强强叫它“道”(强字之曰道),或者叫它“大”(强为之名曰大)。因为“道”太伟大了。它是最伟大的婴儿(先天地生),也是最伟大的妈妈(可以为天下母)。所以,它又是最柔弱的。也就是说,唱反调,就是道的运动;居弱势,就是道的运用;最柔弱,就伟大;反着来,就成功。
也有四种解释,或者四个原因。
实际上我们去看《老子》一书,其中但凡被称之为“大”的,没有一个不是反着的。比如第四十一章的“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上德若谷,大白若辱”;以及同一章的“大方无隅,大器免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还有第四十五章的“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等,都是,也都好理解。需要说明的,是“大器免成”。这句话,一般的版本都写作“大器晚成”(现在已经变为成语)。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写的却是“大器免成”(甲本残缺)。楼宇烈、高明两位先生,认为应该是“免成”,我也这样认为。因为老子这段话,从头到尾都是在唱反调。比方说,方的特点,是“有隅”,但“大方无隅”。音的特点,是“有声”,但“大音希声”。象的特点,是“有形”,但“大象无形”。器的特点,是“要成”。照理说,则“大器”就应该“免成”;晚成,就不对了。晚成,也是“成”么!实际上,按照老子的逻辑和观点,最高级的东西,都不可能是做出来的。你做不出,他也不需要做。黄山是做出来的吗?泰山是做出来的吗?黄河是做出来的吗?长江是做出来的吗?不是。这就是“大器免成”了。所以,在第六十三章,老子就说“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也就是说,你反过来,不做,就能大。这在老子那里,就叫“无为”。而“无为”,大约是可以“无不为”的。
那么,天子、诸侯,为什么要往自己身上“泼污水”呢?
这就是老子的境界,也就是老子的追求。
实际上,就在第七十八章,在说完天子、诸侯必须“受国之垢”“受国不祥”之后,老子做了一个说明。他紧接着说,这就叫“正言若反”。什么叫“正言若反”?也就是“正话反说”。有人正话反说吗?有。谁?天子、诸侯。天子、诸侯怎么称呼自己?孤、寡、不穀。诸侯称孤道寡,天子自称不穀。什么意思?孤,就是“孤独之人”;寡,就是“寡德之人”;不穀,则是“不善之人”。呵呵,都不是什么好词。所以,老子在第四十二章就说,天底下最不好的称呼(人之所恶),莫过于此了。可是,我们知道的情况,却是这些“恶名”,为天子和诸侯独享,是一种最高的“待遇”。别人想用,还没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