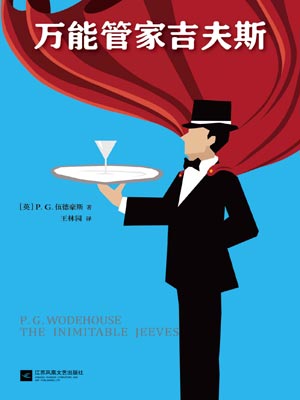第四章 (第5/5页)
P.D.詹姆斯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接着我就看见了他。他被皮带吊在天花板的钩子上,我知道他已经死了。科迪莉亚,那真恐怖!他穿得像个女人,带着黑色胸罩,穿着黑色蕾丝底裤,其他什么都没穿。还有他那张脸!他的嘴唇涂着唇彩,科迪莉亚,嘴唇全都涂满了,就像马戏团的小丑。那样子又可怕,又可笑。我当时既想笑,又想尖叫。他看上去不像马克,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人。桌子上有三张照片。不是什么好照片,科迪莉亚。是女人的裸照。”
她睁大眼睛看着惊恐不安又大惑不解的科迪莉亚。
雨果说:“别这个表情,科迪莉亚。当时的场面对伊莎贝尔来说太可怕了,现在想起来也不舒服。但那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也不是那么不常见的事,也许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性怪癖。除了自己,他并没有把别人拉进来。他并不是想自杀,只是不走运。我想是皮带扣滑动,他根本没机会逃脱。”
科迪莉亚说:“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但这是真的,科迪莉亚。现在我们就给索菲打电话怎么样?她会证实这一点的。”
“我不需要别人来证实伊莎贝尔的话,我早就知道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不相信马克会自杀。”
话一出口,她就知道说错了。她不应该表露出自己的怀疑。可是现在已经晚了,她还有些问题要问。她看见了雨果的脸,对于她的迟钝与固执,他不耐烦地皱了一下眉头。接着她发现了他情绪上的微妙变化,是恼火、害怕还是失望?她直截了当地对伊莎贝尔说:“你说那扇门是开着的,你有没有注意钥匙?”
“在门的里侧。我是出去的时候看见的。”
“窗帘怎么样?”
“跟现在一样,是拉上的。”
“当时唇膏放在什么地方?”
“什么唇膏,科迪莉亚?”
“马克涂嘴唇的那支唇膏。他的裤子口袋里没有,不然警察一定会发现。那么口红到哪儿去了呢?你当时有没有看见它在桌子上?”
“桌子上除了那几张照片什么也没有。”
“那支口红是什么颜色的?”
“紫色,老太太用的那种颜色。我觉得其他人不会用。”
“那么内衣呢,你能描述一下吗?”
“哦,可以。是从玛莎百货公司买的。我认得出来。”
“你是说你认出了这些特别的内衣,它们是你的?”
“哦,不是的,科迪莉亚!不是我的。我从来不穿黑色内衣,贴身衣服我喜欢穿白色的。可那个牌子我经常买。我的内衣都是从玛莎买的。”
科迪莉亚心想,伊莎贝尔可能未必是那家商店的最佳顾客,但是在细节上,尤其是衣着方面,任何目击证人都不会像她那么可靠。即使在当时那种绝对的恐怖和变故下,伊莎贝尔还能注意到内衣的类型。如果她说她没有看见口红,那一定是有人不想让它被发现。
科迪莉亚继续追问:“你动过什么东西没有?比方说马克的尸体,看他是不是死了。”
伊莎贝尔异常吃惊。生活的事她可以从容应对,但是死亡却不行。
“我不可能去碰马克!我什么也没碰,我知道他死了。”
雨果说:“一个可敬、理性、守法的公民会就近找个电话向警方报案。所幸的是,伊莎贝尔不是这样的人。她的直觉是来找我。她在戏院外面等我们,一直等到散场。我们出来的时候,她还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来回溜达。戴维、索菲和我开着雷诺跟她一起到了这里,当中只在诺维奇大街弯了一下,去取戴维的照相机和闪光灯。”
“为什么?”
“那是我的主意。我们显然不想让警察和罗纳德·卡伦德知道马克是怎么死的。我们想制造一个自杀假象,打算让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把他的脸洗干净,让其他人来发现这个现场。可我们没想到伪造自杀遗书,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么细致。拿照相机是为了拍下他的死亡现场,我们不知道伪造自杀现场会触犯哪条法律,但这肯定是违法的。现在你想为自己的朋友做点最简单的小事,都有可能被人误会。为了防止惹出什么麻烦,我们得先保留一些实际证据。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喜欢着马克,但也不想冒着被指控谋杀的风险。不过我们的好意受到了阻挠,有人捷足先登了。”
“跟我说说看。”
“没什么可说的。我们让两个女孩子在车里等着,因为伊莎贝尔已经亲眼看见了,当时依然心有余悸,所以不能把她单独留在车里,索菲也留下来陪她。再说了,不让索菲进去看见马克的样子,这对马克来说也好。科迪莉亚,你不觉得这种心态很怪吗?人们居然会考虑死人的感受。”
科迪莉亚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伯尼。她说:“也许只有当人死了之后,我们才能放心地表露自己的关心,因为那时候他们想做什么也无能为力了。”
“你这话有些刻薄但也不假。不管怎么说,当时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了。我们发现的马克尸体和屋里的状况,与马克兰德小姐后来描述的相符。那扇门是开着的,窗帘拉上了。马克全身只穿了一条蓝色长裤。桌子上没有杂志照片,他的脸上也没有涂口红。打字机上夹着一张自杀遗书,壁炉架里有一堆灰烬。看来这个不速之客做得干净利落。我们没有久留,因为随时可能有人来——也许是大宅里的某个人。当时的确已经很晚了,但这似乎注定是个友人造访的夜晚。当天晚上来拜访马克的人,也许比他在农舍生活期间的还多,起初是伊莎贝尔,后来是那个不速之客,紧接着就是我们。”
科迪莉亚心想,在伊莎贝尔之前,还有一个人来过。杀害马克的人才是第一个到达的。她出其不意地说:“昨天晚上有人跟我开了个愚蠢的玩笑。我离开派对回来的时候,看到那只钩子上挂着一个长枕头。是不是你们干的?”
如果雨果的惊讶是装出来的,那他装得比科迪莉亚想象的要好多了。
“当然不是我干的!我还以为你住在剑桥呢,根本不知道你住在这里。而且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警告我快走开啊。”
“那简直是疯了!那有什么用?别的女人可能会被吓跑,但你不会。我们只是想让你相信,马克的死没有什么可调查的。可那种把戏反而让你更坚定地查下去。有别人想把你吓跑。最有可能的,就是我们走了之后来的那个人。”
“我知道。有人为了马克的事情在铤而走险。这个男人——或者女人——不想让我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不过他可以用理性的方式让我走,告诉我真相就行了。”
“那他怎么知道能不能信任你呢?科迪莉亚,现在你怎么办?回到城里去?”
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随意,但科迪莉亚还是觉察出他内心的焦虑,于是回答说:“我想是这样。不过我要先见见罗纳德勋爵。”
“你准备跟他说什么呢?”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会有办法的。”
雨果和伊莎贝尔准备离开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已经透出黎明的曙光,嘈杂的鸟叫声迎接着新的一天。两人把安托内罗的画带走了。科迪莉亚看见它被取下来的时候,心里有些遗憾,好像原本属于马克的东西从这个农舍被拿走了。伊莎贝尔以专业人士的严肃目光仔细检查了那幅画,然后把它夹在腋下。科迪莉亚心想,伊莎贝尔也许很大方,无论是人还是画,她都会借,但条件是必须及时归还,而且与出借时一样完好无损。科迪莉亚站在门口,看着雨果把那辆雷诺车从篱笆的阴影中开走。她抬起手臂做了一个告别姿态,就像一个疲惫的主妇在匆匆送走最后的客人,接着她回到农舍里。
他们走后,客厅里冷清了许多。壁炉里的火就要熄灭了,她赶紧把没有烧完的柴往里推了推,把火吹起来。她在小房间里不断来回走动,睡意全无。这个短暂而多事的夜晚弄得她心烦意乱,心力交瘁。不过使她备受折磨的不是睡眠不足,而是一些更重要的东西。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害怕了。罪恶真真实实地存在着——不用修道院的教导她也能相信了——罪恶就曾经发生在这个房间里。这里有比邪恶、冷酷、残忍或私利更凶猛的东西。罪恶!她毫不怀疑马克是被人杀害的,而且是这么恶毒的方式!如果伊莎贝尔说出了真相,那还有谁会相信他不是意外死亡,而是自杀呢?科迪莉亚无须从她的解剖医学书中寻找答案,就知道警察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正如雨果所说,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他是精神病医生的儿子,可能听到或者读到过类似的案例。还有谁会知道?也许任何一个见多识广的人都会。但凶手不可能是雨果,雨果有不在场证据。她也不愿相信戴维或索菲参与过这一令人发指的犯罪。但是去拿照相机是他们的典型作风。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同情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考虑。有了这些照片,他们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抖出马克的死亡真相,而让自己免于麻烦。在拍下照片之前,雨果和戴维会不会站在马克扭曲的尸体下面,平静地讨论焦距和曝光?
她走进厨房去泡茶,很高兴摆脱了天花板那只钩子的心理阴影。那钩子不会使她不安了,现在它又像一尊挥之不去的带有魔力的神物。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它似乎开始变大,现在依旧在变大,她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它。客厅无疑变小了,它已经不是私密的圣所,而是幽闭的监室,像执行死刑的小屋,丑陋而令人生厌。就连清晨的空气中也能闻到罪恶的气息。
趁着等壶里的水烧开,她静下心来仔细盘算今天的活动。现在下推断还为时过早,她的头脑中还有太多的恐惧,无法理智地分析新的情况。伊莎贝尔的讲述不仅没有使案件更加明朗,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复杂。还有一些相关事实有待发现。她打算继续执行自己的原定计划。她今天要去伦敦,查看马克的外祖父留下的遗嘱。
离出发还有两个小时。她决定把汽车停在剑桥火车站,换乘火车去伦敦,这样既快又省事。要在伦敦待一天让她觉得心浮气躁,因为这宗迷案的核心显然在剑桥。然而这一次当她想到要离开这座农舍时,却没有感到遗憾。由于震惊和焦虑,她漫无目的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又来到园子里来回踱步,不安地等着出发。最后,她百无聊赖地抓起那把钉耙,把马克没有挖完的那畦地挖完。她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明智。马克撂下的这点活儿是他遭到杀害的证据之一,可是包括马斯克尔警长在内的其他人也都见过这一幕,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替她作证。眼前这些没有完成的工作,依然斜插在土壤中的钉耙,都令人感到难以忍受的恼火。她把这一畦地挖完之后,内心终于平静了一些。接着她又不停地挖了一个小时,最后把钉耙仔细清理一遍,拿进工具棚,把它和其他工具放在一起。
终于到了出发时间。七点钟的天气预报说东南部有雷阵雨,所以她穿上了外套。这是她随身携带的最厚的衣服。自从伯尼死后,她还没有穿过这件外套。她发现束腰的带子变得松垮了,这说明她瘦了。她略加思索后,从现场勘察工具箱里拿出马克的皮带,把它在自己的腰上缠了两道。皮带紧紧地系在她身上,她却没有感到任何厌恶。她不相信马克使用过或者拥有过的东西会使她恐惧或沮丧。这根皮带的分量以及勒在她身上的力度甚至隐隐约约地使她感到欣慰与安心,好像它是一个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