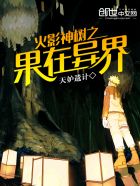第二章 满汉之争中的传教士 (第4/5页)
孙立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这只是一个例子。钦天监算日子和选墓地的是两组人,如果把汤若望单独算,那钦天监就涉及三组不同利益的人。算日子和选墓地的人,当年就对一些细节有不同意见。他们两组人在一些五行分析上意见不一致本来也属正常。长期以来,遇到意见相左的情况,两组商量一下,统一意见就完事了。没料到这次遇到杨光先这样的高手来追究。而且整个审理的大环境对钦天监极为不利,因为现实就是荣亲王下葬不到三年,董鄂妃和顺治就接连去世。这相当于已经坐实了钦天监风水选取有错。所以杨光先提出下葬问题以后,整个审讯的基调不是调查之前的下葬风水到底有没有错,而是在调查错误出在哪里,是谁的责任。大概汤若望也知道这个问题没有辩驳的希望,所以代表他回答的南怀仁神父(当时汤若望神父中风了,说话吃力,朝廷允许他和南怀仁用德语交流,再由南怀仁答辩)完全没有谈理论,一开始就是在划清界限,说汤若望不懂风水,选日期和选墓地他都没有实际参与。
历狱始于1664年,是辅政大臣执政的第四年。从大环境上看,案子发生在辅政大臣打压汉官汉制的大背景下。就连礼部上奏建议给康熙皇帝开蒙,让他学习汉字,辅政大臣都不批准。康熙只能私下从身边的太监那里学习一点简单的汉文。15
埋葬风水选取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埋葬人的八字五行分析,二是埋葬地方和埋葬时间的五行分析。从钦天监官员给出的口供看,他们对杨光先分析的荣亲王八字中的五行属性、五行强弱这些没有异议。双方辩论的焦点是1658年埋葬那一年和那个月的五行以及墓地的方位五行到底应该怎么算属性。概括起来,杨光先认为那一年五行属水,而钦天监说那一年属火。
从现实角度看,这份罪已诏最实际的作用其实是借顺治之口承认了以前朝堂政策中的汉化问题。这就为后来辅政大臣上台以后的一系列变革扫清了道路。比如辅政大臣重整了宫中的管理,裁撤了太监的很多部门,把太监放到了满人控制的内务府之中,废除了太监的权力。这样终于终结了长期困扰历代政治的宦官问题。
而就是这五行属火的分析口供给整个钦天监带来了灭顶之灾。杨光先在看了钦天监给出的口供后,指出如果是属火的话,这个说法只可能出自一本叫《灭蛮经》的历法书。按杨光先解释,《灭蛮经》是有意把五行日历搞乱,然后再把这本书传播到蛮夷之地去混淆视听用的。作为“蛮夷”之一的满人,得知这个解释以后,整个审问的性质就完全变了。钦天监的错误一下从技术失误上升到了反清谋反的高度。用审问者的话来说:“今用《灭蛮经》选择,以壬水为火,埋葬荣亲王,险恶用心。”51
对顺治来说,平衡满汉两个传统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的很多政策也因此在不停地变化。顺治有几年重用汉官以及太监,这些都被视为有违满人祖制的汉化政策。所以在顺治的罪已诏中,才会出现“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这样自我批评的总结。当然这份诏书落款日期是顺治去世当天,历史上也有说法认为,这份诏书是顺治生母孝庄拟定的。不过,无论是顺治还是孝庄的意思,这份遗诏都体现了满汉传习是当时朝堂之争的一个核心问题。
从传统算命风水理论来看,当年钦天监给出的结果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但公正地说这应该都是技术上的失误。但在审讯中,钦天监的人为了自圆其说,就把一些年份的五行按照符合他们测算结果的方向作解释。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技术细节上的解释,会被杨光先抓住把柄,上升到谋反的程度。
对于为何“国治未臻,民生未遂”,顺治总结的原因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简单来说,就是用了汉族的传习,而更改了满人祖制。尽管顺治在位十八年,但是减去多尔衮辅政的八年,顺治实际是十三岁开始亲政,到二十三岁终,亲政仅十年。年纪轻轻的顺治,从满人帝系上看虽然不是第一个皇帝,但他确实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中国的满人皇帝。除了南方南明势力以及各地持续不断的反清复明活动以外,顺治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农耕传统下的汉族统治和游牧方式下的满蒙传统。对于这个问题,顺治没有多少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元代的忽必烈汗(1215-1294)是第一个在北京统治的蒙古皇帝。尽管忽必烈名声很大,但顺治和朝堂上的大臣都知道元代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失败的。忽必烈死后,元代在中国的统治也只持续了七十年。
当杨光先说那年属水的时候,给出了依据,并指出在哪些书上能验证他的说法。同时他质问钦天监说的属火是依据哪本书,钦天监回答不出。而当杨光先说唯一有记录这年属火的书是《灭蛮经》时,钦天监的人也没有找到反驳理由。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乎,苟安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14
满人高层为了确认杨光先的说法,专门派人到浙江、福建等地,寻访了一些当时公认的算命方面的高人,这些人都确认了杨光先的五行分析是正确的。同时这些人也听说过《灭蛮经》,印证了杨光先的说法。其中一位还说《灭蛮经》是中国人所编写,而传至外藩,“使彼用而断根绝后”。这就使整个案子急转直下,刑部看完卷宗后,给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建议是所有钦天监参与占算的人都以“大逆之罪”论处,而刑部引用的刑律中“大逆之罪”的处罚是“不分首从,俱行凌迟处死”。刑部认为汤若望是当时掌印之官,也难辞其咎,也要凌迟处死。后来,和硕康亲王杰书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议后,认可了刑部的谋反认定,同意将参与占算的人全部凌迟处死。52
1661年2月5日,顺治皇帝在染天花后驾崩,年仅二十三岁。在遗诏中,他传位于佟氏所生的时年八岁的玄烨(后来称为康熙皇帝),并任命了四位满人老臣为辅政大臣。这份遗诏,同时也是顺治写的一份罪已诏,承认自己执政期间的诸多问题。第一条,顺治这样写道:
前面已经提到过,由于北京在该案审判定罪后发生了大地震,很多人相信这个案子有冤情。在孝庄皇太后出面干涉后,汤若望被赦免了。不过还是在赦免的批文中写到,汤若望作为掌印之官,“本当”处死,只是念其“效力多年”,免了死罪。但汤若望属下汉官的死刑还是执行了,只是没有凌迟。
满汉路线之争
案情之外,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就是此案议政王大臣会议审理了八个月才结案。对比之下,三年以后鳌拜被抓,同样是和硕康亲王杰书主持审理,议政王大臣会议用了八天就判了鳌拜三十条大罪。为什么汤若望这个案子会拖那么久?这是因为有满人高层势力在暗中保护传教士,也就是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背后的佟家势力,以及豪格的正蓝旗。佟家是康熙母亲的娘家,一直是满人中的大家族,康熙即位以后,佟家作为外戚,势力更超从前,朝廷各个部门都有佟家的人。
满人在整个案子中的关键作用其实随处可见。首先这个案子不是朝廷系统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在处理,而是由凌驾于朝廷系统之上的满蒙权贵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员在负责调查。13其次,由于整个案子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负责,所有案件的材料都是用满文书写的;有汉人证人出席的证词也都直接翻译成了满文,没有原始汉文记录。这两点就已经说明这是一个满人办的案子,他们才是控制整个案子走向的一方。最后,从历史的大环境上说,案子发生在顺治死后四年,康熙尚幼,还未亲政。这段时期朝政由四大辅政大臣打理,有些历史中,也称这段时期为“鳌拜专权时期”。1669年康熙智擒鳌拜是历史、小说、影视剧中都广为流传的桥段。而从1661年顺治驾崩算起,鳌拜专权时期持续了八年。对传教士来说,鳌拜专权时期的历狱一案让他们认清了世道,明白了该如何在满人的天下生存。而就这个案子来说,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关于风水的案子会在选址下葬数年以后突然被翻出来?这一切就得从顺治驾崩说起。
前章已经讲过,汤若望与安文思、利类思虽然同属耶稣会,但由于各种私人矛盾,双方一直不和,在北京各有各的教堂,各传各的教,几乎没有往来。历狱一案开始以后,汤若望由于已经中风,所有辩护相关的重任落到了当时汤若望的助手南怀仁神父身上。南怀仁和汤若望不同,他跟安文思和利类思有良好的私交。由于杨光先在历狱开始时还连带打击整个天主教,这样安文思和利类思就走到了南怀仁身边,一起对抗杨光先。安文思和利类思背后的佟家势力,也在杨光先攻击天主教的时候被牵扯进来。当时在江南长期资助天主教的佟国器被召回北京,接受审问。佟国器是封疆大吏,之前在江南几个省都做过巡抚。从审讯记录来看,佟家势力很明显干涉了审讯,佟国器在承认给教堂捐过一点小钱后,很快就被放了出来,审讯也不继续纠缠他和天主教的关系了。53刑部满人尚书尼满也暗中为汤若望开脱,把罪过推到汉官身上。后来显亲王富绶专门密奏,说汤若望其实是“专司天文”的,因而选择错误不应该罚他。54显亲王富绶是豪格的儿子。尽管密奏上只有富绶一个人的名字,但这说明汤若望和传教士并不是在孤军奋战,他后面是有一个满人权贵群体在相助着。
整个案子审了八个月。由于风水对错、安葬时间等都涉及历法计算,历史上又称此案为“清初历狱”。汤若望这位洋神父是案子的中心人物,因而这个案子长期以来被视为中西文明冲突的一个案例。11但这种文化冲突理论有个根本缺陷,就是没有考虑作为统治者的满人,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满人在中西冲突的二元对立理论中直接被忽视了,或者说因为最后的判决是偏向杨光先,中西冲突理论就把满人简单看成了汉人文人士子的代言人。12而且最后的结果,好像是杨光先获胜了,但实际上传教士基本没有损失。整个案子最大的受害方是钦天监里的汉人,核心成员都被处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