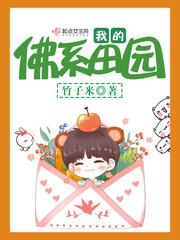跋 (第2/5页)
孙立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第一句:“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巴拉新法。”“阿尔巴拉”就是代数,是Algebra的音译。康熙皇帝外出,一路上还和他的皇子一起研读代数这个当时全新的数学科目。这说明什么?如果在旅途的火车上,我们看到一个人拿着一本代数书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康熙整篇谕旨,说的是他试着在理解这本代数书,但明显没有看懂,最后指示他的奴才把这本书拿去让西洋人共同“细察”,把问题写明白。
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是定义出了虚数概念。虚数在英文中叫 Imaginary number,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想象出来的数字”。虚数最早是由笛卡尔提出,但在与实数一起进行运算时还有大量实际操作问题。而虚数相关的各种问题完全解决是在18世纪中期,也就是在中国的乾隆年间。康熙想要知道的问题可能现在看起来不难,但放在当时都是大问题。康熙在得不到好的代数书翻译的情况下,让传教士直接把他们能找到的所有西文代数书都交给皇三子。”六十多岁的康熙还寄希望自已能和他的皇子一起把代数弄明白。在数学中,“元”“次”和“根”等专门术语都是康熙翻译的。
现当代史家引用到这份谕旨都集中在康熙的最后两句,评点代数“算法平平”“可笑”上。这几个词就是吸睛的冲突部分,用来说明康熙自大无知,耽误了西学、科学引入中国。3除了把这几个冲突字眼拣出来,没有人关注这段话的前半部分,也没有人想要理解为什么康熙说“算法平平”“可笑”。
除了在历史细节上经不起推敲,基于清初传教士来华而衍生出的各种文化冲突理论还有一个先天缺陷:就是无法解释传教士事业在康熙时代的辉煌。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真的不能调和,西方科学和中国传统思维有冲突,那么为什么传教士在康熙年间能成功,教徒人数成几何级倍数增长,西方知识大量涌入?康熙一朝就是六十一年。六十一年放在历史长河中很短暂,但这也是传教士在中国,和中国百姓一天天、一年年过出来的六十一年。不能因为后来雍正禁了教,就选择性忽视之前调和的日子。传教士在康熙朝得到了各种优待不假,但百姓入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寺庙、道观,教堂,老百姓选择去哪里,到底有没有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他们是在用行动给出答案。
谕王道化:朕自起身以来,每日同阿哥等察阿尔巴拉新法,最难明白。他说比旧法易,看来比旧法愈难,错处亦甚多,鹘突处也不少。前者朕偶尔传于在京西洋人开数表之根,写得极明白。尔将此上谕抄出并此书发到京里去,着西洋人共同细察,将不通的文章一概删去。还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总无数目,即乘出来亦不知多少。看起来想是此人算法平平尔,太少二字即可笑也。特谕。
这又涉及一个历史的评判问题。历史应该最少有两次评判。一是当时的人-历史参与者流露出的主观感觉,这可以算作一种评判。二是后来人综合历史上下文的评判。这两种评判可以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评判不能无视当时人自身的感受。比如藏传佛教中一路几千公里磕长头的苦行。如果一位苦行的信徒成为了历史人物,变成了历史研究对象,这时候他磕长头朝拜和朝拜时的满足与期待才是历史中的存在。后来人的历史评判,需要在当时人的行为和感受基础上来做评判。如果完全不考虑当时人的主观感受,而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认为他的苦行没有价值和意义,那就跟当时历史没有了关系,这种评判严格讲也不属于历史研究。本书第二章讲到杨光先时,其实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杨光先的书和言论在当时没有得到士人的认同,没有引起反响。因而无论他去世一百年后有多少人关注他的观点,历史的事实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书当时没有引起反响和认同。所有明末清初相关的历史论述,也都应该建立在杨光先在当时没有得到主流文人认可这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而鸦片战争以后,杨光先的论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重视,被研究,这属于另外一段历史,和明末清初的历史应该区分开来。两段历史的不同,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派别,就是后世“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比如杜甫,唐朝以后各个时代对他的作品有不同的评论和看法,但这些评论和看法不能当成杜甫自身历史的一部分。”
除了对薛凤祚、明安图这样的人物视而不见外,传统文化阻碍西方科学传入的论说还经常对历史材料断章取义。像本书前面提到过的康熙晚年与皇子们一起学习代数的事,就被用来说明康熙阻碍了西方科学的进入。这件事很多书中都有提到,因为有一张康熙亲笔写给他奴才的谕旨存留,谕旨图片和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