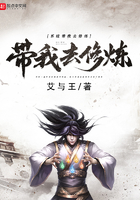跋 (第3/5页)
孙立天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明末清初传教士一批一批来到中国,他们就是当事人。在我们做出任何关于当时中西文化对比的判断时,应该首先看他们怎么说。传教士来到中国后,确实观察到了中西文化方方面面的差异,而且还留下了各种记录。但他们认为那些文化差异是冲突,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吗?显然不是。全球化之初,商人和传教士是最早走遍世界的两大群体。跟牟利的过往商人不同,传教士到了世界各地都需要深度融入当地社会。因此,他们的记录都是他们在当地生活后的切身体验。当时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在定居中国前,都到过许多国家,也了解世界各个地区的文化差异。对他们来说,中国社会和文化是很包容的,是在传统文明发达的地区中很有可能接受基督教的地方。当他们在中国发现已在开封定居几百年的犹太人,并得知他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信仰时,就感叹过传统中国的包容。当时耶稣会神父还去到印度的莫卧儿帝国(1526-1857)。他们也走入了当时莫卧儿帝国一代明君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1542-1605)的皇宫。但是面对伊斯兰势力,耶稣会神父能够发挥的空间很小。1同时,意大利的耶稣会神父伊波里托·德基德利(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在1716去到了中国西藏。当时西藏知道一些耶稣会神父在北京的事迹,因而伊波里托在西藏还受到了款待,被允许留在拉萨学习藏语、佛教和西藏文化。西藏并没有排斥这位意大利去的神父,还允许他建立一个小的天主堂(一个小房间)。只是伊波里托神父自己发现很难把基督教传进西藏,很难找到信徒。”如果按今天流行的经济学观点,我们把信仰需求看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可以说基督教作为一款信仰产品进入不了西藏市场,因为那里的本土信仰产品已经足够强大。12但当时的内地不一样,基督教作为信仰产品是能够进入到内地的,内地的百姓和主流文人都抱有一种开放的观念,把基督教当作一个外来的新产品在看待。尽管来华的传教士在对待中国传统习俗的态度上有分歧,但那是他们内部的分歧。他们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土地能容纳西方科学和宗教这个大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修会都在增派人手到中国。传教士内部的分歧,就像今天跨国大公司不同部门之间对产品如何进入中国市场,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消费习惯,以及如何让产品本土化的过程中有分歧是一样的。佛教于汉代进入中国以后,如何让佛教本土化,如何接入中国传统观念和文化,也是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问题。
牛顿(1643-1727)和康熙(1654-1722)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如果把牛顿看作欧洲科学革命奠基人的话,那么康熙一朝就正好处在西方科学革命爆发的前夕。当时除了康熙自己和他的皇子们学习西方知识以外,康熙还在宫里组织八旗子弟来学。比如在宫里面学习的正白旗蒙古族人明安图(1692-1763),看到了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牛顿无穷极数公式后,就用从传教士那里学来的西方几何证明方法,证明并推导出了卡塔兰数。明安图还推导出了一些衍生公式,这些公式在翻译成现代数学语言后,陆续被国外学者证明。卡特兰数在函数、离散数学中广为使用。它是卡塔兰(1814-1894)在1838年推导出来的,比明安图的证明晚了一百年。2我们知道有明安图这样的八旗子弟存在,就理解为什么当时传教士担心中国人学习西方知识太快。他们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
对于当时的传教士和教皇来说,中西文化没有冲突,冲突的只是他们天主教内部的不同派别。罗马教皇收到康熙的红票,给康熙的回信中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们对教内做出的规定会让您不高兴。”天主教即便是在欧洲内部争论时,对孔子以及儒家传统都抱有十足的敬意,认为孔子提倡的“慎终追远”、重视丧葬、敬畏神灵是和天主教教义精神暗合的。他们并没有想过要反对这个传统,而他们要规定的只是受洗的教徒,要他们坚持心中只有一个神灵,就是天主,人教之后不能再求祖先等其他神灵保佑和庇护了。在这个思路指导下,他们规定了教徒哪些传统活动能参加,哪些不能。在传教士和教皇眼中,中西文化在某些具体操作上是有差异的,但不是互相冲突,是可以共存的。后来的历史其实也证明了传教士的基本判断。当儒家文化圈里的中日韩决定引进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很快速从容地做到了。在引进西方文化的历史进程中,这几个国家真正担忧的是西方文化是否引进得太多、太快。
康熙末年的传教士也证明了金尼阁的判断。当时传教士真正头痛的问题是中国人学得太快了,他们担心以后没有科学知识继续教给中国。如果把这些传教士看作西方科学的老师的话,那么他们对中国学生们的评价是极高的。传教士到中国的目的是来传教,而他们为方便传教,选择用教授西方科学技术作为先导,来融入中国士大夫群体,这不已经极大地说明问题了么?
哪怕在雍正禁教以后,也没有任何传教士认为这是中西文化冲突所致。一切不过是宫廷政治罢了。雍正禁教在当时传教士看来也只是暂时的挫折。康熙初年鳌拜时期,在汤若望被参劾后,传教士的教堂都被没收了,后来又靠南怀仁东山再起。雍正时期北京的传教士就在等待下一次东山再起的时机。1735年,雍正去世,乾隆登位,康熙朝就活跃于北京官场的巴多明神父马上认为这是一次机会。他找到了内阁官员和康熙的皇十二子,让他们帮忙活动,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折子。尽管最后巴多明没能说动乾隆,但这份折子充分说明了传教士的希望和等待。
除了基督教引发的中西文化思考,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数学、科学,也是文化理论找材料的热门领域。后来的历史中,西方科学没有在中国生根发芽,这是现当代学者都知道的。于是有很多“大”问题伴随这个结果而来。西方科学没能传入,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还是传统政治制度的问题,还是二者兼有?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其实有两个预设,一是西方科学没能传进来,二是没能传进来是传统中国的问题。这些反思型的预设,都是拿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历史结果反推出来的。但在实际的明清历史中,这两个预设都是不成立的。传教士明末到中国,就发现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兴趣不大,反而只对西方的数学、科学有兴趣。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在万历年间到达杭州,在那里传教两年后,返回罗马报告中国的传教事业。除了教会内部的问题,金尼阁回去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告诉欧洲,中国人对欧洲的自然科学、技术和数学感兴趣。他在欧洲四处募捐,买了7000册关于欧洲各方面的书籍,于1620年运到中国。西方科学技术图书是金尼阁购买书籍中的重要部分,这其中就包括当时欧洲最新的哥白尼日心说的证明等。而帮金尼阁选购图书的是邓玉函。邓玉函是伽利略的学生,在欧洲就是一流学者。金尼阁和邓玉函人华后,和江南士大夫交往频繁,他们费尽心力把西方的书籍运到中国,就用行动说明了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社会能够接受这些书籍。
乾隆登基后,尽管他没有像康熙那样允许天主教传播,但和雍正不一样,乾隆是愿意使用传教士的。圆明园的喷水池部分就是传教士设计,仿照欧洲宫廷建造的。近年来颇有名气的十二生肖兽首,就是安装在圆明园里用作喷水龙头之用的。巴多明神父年迈之时,还曾上奏乾隆,说自己年纪大了,希望能允许两个年轻传教士来北京照顾他。乾隆允准了。来的两个传教士就是来继承他北京的教堂的。巴多明于1741年在北京病逝,是经历了康雍乾三朝的元老。像巴多明一样在北京等待机会的传教士还有很多。鼎鼎大名的郎世宁也是这样。康熙朝就到北京的他,一直在宫廷里作画,乾隆的母亲就很赏识他,还坚持要乾隆给郎世宁安排个官职,发薪俸给他。13郎世宁从雍正1724年禁教,一直到他1766年去世,又在北京待了四十多年。他到死都还在等待机会,希望有一天能让天主教被朝廷重新认可。乾隆登基后不久,在澳门的传教士专门开过会讨论天主教在中国是否还有希望。会上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困难来自于中西文化差异或者是文化冲突,他们都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皇帝的想法。他们都寄希望于北京的传教士能像南怀仁当年一样,找到机会。乾隆中期以后,以郎世宁为代表的宫廷传教士,通过他们的努力,确实也让乾隆对传教士的看法有所改变。乾隆不仅越来越多地使用传教士,还像康熙一样把传教士召入了他的内务府。一些文件显示,传教士又开始找内务府,而不是朝廷部门来处理他们在北京生活上的具体问题。“现存的奏折中可以看到,1760年代后,乾隆又像康熙一样,命令两广总督选送有技术的西洋人到北京。而且1778年以后,乾隆还几次问询沿海官员为什么没有有技术的西洋人前来。乾隆的这些谕旨,最直接地说明传教士耐心等待时机的既定思路是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