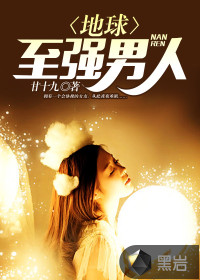黏性劳动 (第3/5页)
孙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街头“鄙视链”
李建平,30岁,河北衡水人,房山良乡镇的众包骑手,于2016年加入“美团”,是为数不多的我采访到的夜班骑手。李建平每天的工作时间相对固定,上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下午5点到晚上8点以及午夜12点到凌晨三四点。李建平的家庭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他有一个小孩,五岁。老婆全职带孩子,负责一日三餐伙食。午高峰1点左右,李建平雷打不动回家吃饭。吃完饭开始睡觉,为晚上跑单做准备。
在聊天时,虞叔以及其他骑手戏称众包骑手为“游击队”、专送骑手为“正规军”。随着平台招工和派单策略的改变,外卖骑手“灵活”“自主”的劳动感知越来越弱,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工作时间、配送订单总量越来越严格的要求。“强控制”再一次成为骑手工作的普遍要求。对于专送骑手来说,他们有了固定的10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而对于众包骑手来说,他们不得不因为“僧多粥少”的情况而主动增加劳动时间。
半夜也会跑。像曼玲粥店、炸鸡店、麦当劳都会开门。只要肯等,还是有单。最好的时候能在这个时段拿两三百。等单的话,就在这些店里,找个椅子。店里没什么人,就一两个值夜班的。困了就趴一会儿也没事。不会赶你走。慢慢等。
外卖平台业务链条的不断修正完善也伴随着其对于外卖骑手劳动的“正规化”和“职业化”要求。企业端的招工导向以及其与政府部门的合作成为重要的推手。2021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布了《网约配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年版),将“网约配送员”划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并明确了各等级配送员所应掌握的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至此,外卖骑手这一新兴的、流动式的劳动形态被收编为正式的劳动岗位,名为“网约配送员”。骑手开始逐渐有了需要遵从的职业技能、职业标准等层面的规章制度。
李建平跑众包夜班,因为2020年以后,单单每日午晚高峰的订单并不足以养家糊口,他需要跑更多的单子。但是白天其他时间段众包骑手众多,分到的单子并不多。于是他选择了晚上,人少,竞争也小,相对单子多一些。“你要相信,总有夜猫子要吃饭!”李建平笑着说。李建平是个实际的人,喜欢穿一件军绿色的大衣。他说等待的时候不想事情,也不会伤感,来得多就能赚得多。但是到了凌晨两三点钟睡意袭来时会很困,为了防止自己听不到订单提醒的声音,他会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
我与调研小组在2018—2021年针对北京骑手的跟踪调查问卷发现,四年间,北京地区的全职骑手人数越来越多,从39.96%涨到了61.54%,而兼职骑手的比重则从60%左右下降至 38.46%(参见图13)。这一结果印证了众包骑手一直以来的抱怨——在以消费者满意度为导向的市场扩张格局下,平台更加青睐稳定、可靠的专送骑手而非上线时间灵活的众包骑手。于是,无论是在招聘还是订单派送上,平台日益重视专送骑手的配置,以此来保证7天24小时的配送运力。这样一种策略导致的结果便是众包骑手订单量和单价的缩减。当然,在这一数据中,全职骑手里面也包含“全日制”跑单的众包骑手,但是相较于专送骑手,他们所占比例较小。
漫长的等待成为李建平跑夜班外卖的主旋律。有一次凌晨,我在小区周边的商场处看到了几个值夜班的骑手。街道上灯光暗淡,只有零星几家餐饮店开着门。透过昏暗的灯光能看见骑手穿着蓝色或黄色的外卖服,很好辨认。一些骑手聚在路灯下,有的趴在电动车上,有的蹲在旁边,也有的坐在顾客稀少的餐馆里睡觉或者玩手机。夜里的街道非常安静,偶尔能听到他们交谈几句。
在前文中我们曾说过,平台的运营逻辑核心是提升用户使用感知。所有外卖平台都将用户的使用体验看作重中之重,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平台的订单量和业务量。而用户体验的最直观感受来自送单的及时率和准时率,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平台对于骑手的运力做出综合调配。随着业务链条的不断延伸,平台将重心由众包转向专送。
夜班骑手需要迎接漫长等待的考验,需要“黏在平台上”,通过耗费大量的时间来换取一定的单量。而随着外卖就业人数的不断增长,这样的劳动状况越来越普遍。通过分析过去四年的问卷数据发现,全职骑手在过去四年的平均劳动时长明显增加。在2018年,劳动时间超过10小时的骑手有36.5%,到了2021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62.6%。这意味着,骑手在平台上的劳动“黏性”明显增加。
在平台对于站点的考核中,骑手的运力考核是非常核心的指标。概括来说,运力考核指的是某一区域的订单配送能力,尤其是在高峰时段,平台需要尽力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将所有订单派送完毕,而运力保障的前提是充足的外卖骑手在线。例如,平台会定期对其管理的所有外卖站点进行排名,运力强、送单量大的站点排名更靠前;运力弱、骑手在线人数少的站点则排名靠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