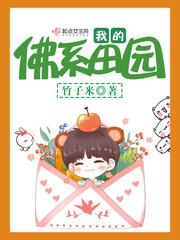拥抱未知 (第2/5页)
孙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在送单的过程中,女骑手慢慢习惯了在骑手身份和性别身份之间快速切换,以确保自我劳动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作为高强度、重体力的职业,外卖配送一直被认为是高度男性化的。虽然进入门槛低,但是它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女性在该领域的留存十分困难。纵观女骑手的劳动实践,在逐步适应外卖劳动后,她们会有效地利用和“盘活”自己的既有资源,其中既包括传统的女性性别气质,如仔细、谨慎、耐心,同时也包括她们从家庭场域“移植”而来的交流技巧、社交技巧和亲情支持。这些优势有效地帮助女骑手在劳动条件艰苦的外卖行业留存下来,甚至有的还会因此“翻盘”,将性别优势转换为劳动优势,成为所在站点或者片区令人羡慕的送单能手。
之前不会看导航。站长教了我好几天,我还是不会,太难了。以前在家里也没什么需要(看导航)。有一次找顾客的位置,不明白导航的意思,就在原地打转,二十多分钟才找到。这个事(跑外卖)不能慢慢干,要跑,使劲跑……一个高峰期下来,心脏怦怦跳,半条命快没了。
女骑手跑外卖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体力。“干外卖是体力活,赚的是辛苦钱”,这是她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对于女骑手来讲,这里的“体力”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单量大的时段需要持续高强度的体力支撑,二是在她们生理期出现不适的情况下请假困难。尤其是做专送,为了保证团队绩效,骑手通常很难请假。卫玮是一名专送骑手,四十岁上下的她在2019年与丈夫离婚,从湖北只身一人来到北京打工。她长得略胖、白净,笑起来有两个酒窝。遇到生理期,卫玮浑身难受,肚子也不舒服。她鼓起勇气跟站长请假。站长虽然表示理解,但迫于团队“人效”压力,仍然没有答应她,而是让她跑完一天的最低绩效——十单之后再休息。“那能怎么办,挨着跑呗,十单一上午能跑完。跑完了回家躺着。”很多时候,一些女骑手难以承受这样高强度的体力和长时间的劳作需求,不得不从专送转为时间更加灵活的众包。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身兼家务劳动或者母职劳动的女性往往会面临身份的冲突。平台化的数字劳动规则如高效、快速、及时等不断规训着女性,鼓励她们建立一种职业化的身份。这种规训将女性以家庭为核心的性别身份转变为以顾客需求为核心的服务者身份。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需要隐藏既有的来自家庭领域的性别化身份,转而变成一个追求效率、善于把控时间的骑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女性不得不由在家务劳动中“主动安排事务”的角色变为听从平台、站点、顾客的“被安排”角色。在诸多劳动实践中,她们对这一转变十分不适:
另外一个问题是驾驶。驾驶领域的性别刻板印象广泛存在于社会建构的方方面面,外卖领域也不例外。同女司机的性别污名化一样,女骑手经常会被贴上“不擅骑车”“方向感差”“路痴”这样的标签。这样的刻板印象通常由女骑手和周边男性共同建构。前面提到的老高和梁子是夫妻档跑单,老高负责骑摩托车,梁子负责看导航。访谈时,两口子对于女性“没有方向感”的说法都表示认同。老高直言不讳地说,女骑手方向感不好;梁子也主动承认,自己在给老高指路时会出现方向错误。
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
梁子:女的么,都有一点路痴。他(指老高)是活地图,我说一个大致位置,他就能找到。我呢,完全找不到。
与男性打成一片成功地帮助柳方克服了心理上的羞耻感和孤立感,她不再像刚开始跑外卖时那么唯唯诺诺,有时候甚至可以在街头很大声地与男骑手逗乐、开玩笑。当然,这样有效的融入并不多,众包的女性多被困于母职需求中,劳动时间相对灵活,难以像男性骑手那样形成持久的街头社群关系。
老高:女同志没有方向感,在自家周边还丢呢,方向感很差。她(指梁子)的外卖群,经常有女同志丢餐了、找不到路。逗死了。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是慢慢习惯了街头人们并不怎么关注的眼光,孙丽丽和柳方在后面几个月的跑单过程中变得大胆了起来。柳方开始尝试在等单的时候跟男骑手主动搭话,问他们一些问题。一旦迈出第一步,打破尴尬,她开始发现身边的男骑手其实“比较好相处”。有的人听说她是新手,会热情地给她讲一些抢单的技巧,告诉她如何根据远近、楼层、餐品来挑选“好单子”。柳方逐渐开始知道其中的窍门。有的骑手在她送餐着急的时候,还会主动帮她在送餐柜上找餐。几个月后,柳方慢慢地和附近的众包外卖员混熟了,知道了骑手们相对固定的聚集地。在没有单子的时候,她会主动跑去聚集点找人聊天。有一次晚上我们找她做采访时,她甚至跑去了男骑手的宿舍,跟他们一起聊天、玩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