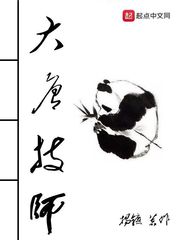拥抱未知 (第4/5页)
孙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受到体力和驾驶的双重“标签化”,很多女骑手在送单过程中会选择遵从、援引传统的性别规范来策略性地化解自身遇到的困难。例如,一些女骑手会在劳动过程中主动承认自己是一名体力弱、方向感差的女骑手,并乐意寻求男性骑手的帮助。这与马丹所研究的女性卡车司机的策略不谋而合,即女性会灵活使用自身的“性别工具箱”,“在不同的劳动情境下辨认出性别突出性之不同的程度与方向,以采取与该情境相对应的性别策略”。这样的传统性别规范往往是女骑手“翻盘”的开始。
拉珍是一个藏族姑娘,来自四川康定。2021年采访她的时候,她二十岁整,已在北京跑了一年外卖。在此之前,她一直在成都和老家之间往返工作,并在成都跑过半年外卖。
利用“弱女子”的身份,女骑手会积极调度自身主动性来寻求帮助。例如,有的餐品含有矿泉水、西瓜时,女骑手难以承担其重量,会主动与顾客或者周边热心人士沟通,请求帮助;遇到路途较远或者难以定位的情况,女骑手会求助身边的其他骑手;甚至在送单超时引发顾客不满时,女骑手也会更加耐心地与顾客交流。部分顾客在看到来者是一名女骑手时,也会“心生怜悯”而化解不满情绪。莱奥波尔迪娜·福图纳蒂(Leopoldina Fortunati)在谈及女性的社会再生产劳动时也表示,沟通和交流虽然是家庭场域重要的“非物质劳动”,但为社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平台资本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依靠社会关系和熟人网络所形成的供需关系链条,转而关注服务的正规化和标准化差异,要求外卖骑手呈现情感劳动“表演”以建立与顾客的良好关系、突出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对此,相较于男骑手在情感劳动方面的无所适从,女骑手对于情感劳动的表现则更加得心应手、细致入微。
我在调研时经常看见诸如此类的场景,一边是男骑手三五成群地抽烟聊天打游戏,一边是一个或稀疏的几个女骑手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单,并不怎么说话。女性的难以融入尤为明显。不少学者曾论述过职业或行业劳动实践中的性别藩篱,朱迪斯·M.杰森(Judith M. Gerson)和凯西·佩斯(Kathy Peiss)使用了“边界”(boundary)这一概念。她们认为,性别的边界一方面有划分类别的功能,另一方面展示了社会空间分配上的性别关系,它彰显着一种微妙的彼此隔绝的关系,即“谁应该被接纳,谁应该被排除”。企业文化、夜间生活、酒吧文化等都带有显著的性别边界感,对男性气质的召唤往往使女性难以融入。多数女性在访谈时都会提到家人劝阻自己跑外卖,认为这份工作“不好”“不体面”。这种不好并不是说收入不高。相较于工厂,跑外卖的收入其实更加可观。“交通事故”“抛头露面”“风吹日晒”成为主要的刻板印象。在实际的劳动实践中,女性走上街头也的确会遇到性别审视的问题。
我在调研中发现,女骑手在“示弱劳动”中并没有极力压制自己的性别身份,而是有效地将性别身份与骑手身份进行对接和融合。通过继承传统父权制下的性别标签,女骑手在平台劳动中努力寻求自己的优势。她们在这一过程中卷入了情绪、情感、身体表征等帮助与人进行交流、联结的各种“软技能”。下面是一些女骑手在访谈时给我传授的跑单经验:
那时候我不认识他们(男骑手)。他们在广场边上,一排排在那儿等单子。我不好意思跟他们说话,又不知道他们会对我是什么态度,就一直没理过他们。如果在那边,我就会一个人躲在后面。
和保安打交道,要嘴甜一些。不礼貌的话,保安有时候就不会给你指路,不告诉你这个小区有多大。
自认为丢人或者羞耻这种情绪在女性刚进入外卖行业时尤为突出。作为初来乍到的“少数人群”,不熟悉路况、对外卖一知半解,难免会担忧和害怕。“有点担心”“不知道自己行不行”等话语常被她们挂在嘴边。刚开始跑单时,孙丽丽不好意思与男骑手走得太近。临近午休,当骑手们三五成群坐在路边或躺在电动车上聊天时,孙丽丽很羡慕,但她并不靠近。她说自己“不好意思过去”。
有些男的等餐着急了,跟餐厅干架。还是慢慢说比较好,人家也能理解你。
孙丽丽以前在河北老家种过香菇、做过餐厅服务员,但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跑外卖。2019年冬天,丈夫因为脑血栓住进了医院,家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儿。一下子没有了经济来源让她很慌张。孙丽丽从朋友的丈夫那里得知,在北京跑外卖能挣钱。“说第一个月挣了六千,第二个月七千,到后面能挣到一万多。”孙丽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可是家里人并不同意,觉得太危险,让她继续留在县城工作。她兜着县城找了一大圈,没有地方收留她。家人无奈松了口。2020年春天,孙丽丽来到北京,在朋友丈夫的帮助下,进了北京西城的一个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