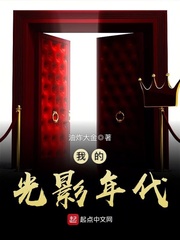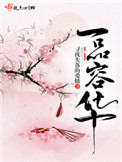时空的阶层感 (第1/5页)
孙萍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阻碍
对于骑手来说,一方面,他们需要等待消费者的订单,而订单到来的时间并不确定;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消费者在订单配送过程中对时间的掌握感,平台会向消费者展现订单派送的全流程。外卖员执行接单、到店、送单、送达这四个步骤,都需要通过手机的 App确认,这种同步性操作确保顾客可以实时查询自己的订餐进度,从而根据订单来安排时间。“即时满足”是平台对时间使用进行层级划分的结果,利用一部分人的时间去服务另外一部分人而实现“时间套利”的盈利逻辑。正如杰森·法尔曼(Jason Farman)所言,关于“等待”的技术性更新中内隐着“谁该等待”以及“如何等待”的文化期许。外卖员是平台语境下“该等待”的人群,他们在时间的支配上看似具有自主权,实则被平台切分成了具有随机性和随时性的存在。这在无形之中建构了骑手与消费者的区隔感。
电动车
对于送外卖这样的随选、按需劳动来说,时间已成为一种十分严苛的管理机制。这里的机制,指的是时间作为一种规训结构如何在与个人、机构、社会交互的过程中明确并强化规则和要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于工人劳动时间的塑造成就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在具体的实践场景中,对于时间的掌控塑造了多种多样的互动场景和劳动形态。例如,加里·艾伦·法恩(Gary Alan Fine)在对餐厅厨房的研究中发现,厨房工作人员会根据餐厅制定的上菜流程和实际情况来对工作的节奏、周期、时长和时机进行管理。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监控时间的诸多手段和工具,如帮助工作人员提高产出效率的 App、上下班的打卡制度、实时追踪产品产出的工作软件等,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人对于时间的具体感知。结构性机制使个人不得不认同并按照结构性时间设置开展社会实践,“同步性”和“重新考量”成了时间机制中不容忽视的存在。
电动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电动车以其便捷、灵巧的特性迅速成为人们的重要交通工具。随着外卖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逐渐发现,电动车成为人们餐饮路上“解决最后几公里”的得力助手。现如今,电动车已经成为外卖骑手鲜明的职业标志。街角巷头,骑手们的聚集处也迅速衍生出了“电动车社群”,一排排带着餐箱的电动车停靠在拥挤的路边,成为一道城市独特的传播景观。
类似的关于时间的抱怨我经常能听到。我无从考证平台上的时间计算是否比日常生活中的时间更快,但是骑手对于时间体验的不满背后,是平台重建“消费者-骑手”权力关系的写照。毫无疑问,消费者的实时需求被放在了首要位置——一种消费者需要被“即时满足”的逻辑得以建立。在时间的分配和协调中,外卖骑手的时间安排往往需要服从消费者的需求。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德烈亚斯·赫普(Andreas Hepp)认为,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高效、快速的传输成为可能,同时也将一种“立即执行”的意识观点带到人们的工作实践中。当信息传输的速度足够快,人们开始变得不耐烦,对“即刻享乐”和“实时裁决”的需求变得越来越高,而这种“对于高效的崇拜”很大程度上成了信息化社会发展的主流时间秩序。
作为现代社会的物流媒介,电动车联结并参与形塑了复杂多元的空间、边界关系。其中既包括骑手本身,也包括一系列关注、强调边界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我的调查发现,基于电动车的流动性是创造骑手与其他人群尤其是消费者空间区隔的重要来源。
我发现,平台上的秒快,秒针走得快。你知道不?一分钟比咱们平常快一些,一会儿就没了。这样更容易超时。
骑手的送餐路径展示了从餐饮店到顾客位置的移动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从公共空间到私人空间的地理转移。在此过程中,空间的准入权和使用权往往会成为问题,而门禁、楼梯或者电梯往往会阻碍电动车的流动。高档小区、写字楼等地理空间往往会限制外卖员和电动车的进入;商业大厦、购物中心、娱乐场所等虽然允许电动车进入并停放,但不允许其停靠在消费者、客户的停车区,而是要求骑手将电动车停放在后门、侧门等其他不显眼的区域。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避免“阻碍交通”或“影响市容市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骑手则不得不走路进入门禁,将餐品送至顾客手中。
众包骑手一旦超时,配送费扣50%;如果超过10分钟,配送费扣70%。一趟下来,本来就没有几块钱,相当于白跑了!
在山东青岛的一些区域,外卖骑手的车上除了配备餐箱,还绑着一个双轮的平衡车。这是因为有些小区面积太大,步行送餐耗时耗力,为了节省时间和体力,骑手自掏腰包购置了平衡车。到了小区门口,当他们的电动车被拦下时,就骑上平衡车,可以快速找到顾客所在地址。但是平衡车价格不菲,并不是所有骑手都有钱购置。
算法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数据思维而非共情思维。这种数据思维所展现出来的是人力所不能及的计算、预测与匹配能力,而且随着数据资源的不断积累,人工智能算法依然在拓展它的应用边界。但是这样的算法思维终究只是一种“数据主义”思维,它将所有的人、物、事和关系化约为简单、平面、可计算的理性逻辑,排除了与人交互的共情感和伦理性。例如,在平台算法的计算逻辑中,并没有包含一种算法素养——这种算法素养能够告知算法系统,骑手的配送时间无法被无限制地压缩。也是因此,在实际送餐过程中,一些外卖骑手对后台算法的时间管理非常不满。
大型商场不允许外卖员将电动车停在门口,而要求放在商场后门等区域。但这些区域无人看管,容易发生偷车问题,这令骑手在送单时提心吊胆。马兰是北京东四环大郊亭的外卖员。她头发乌黑,梳一个长马尾,戴上头盔依然能被轻易地认出来。2019年秋天,她在北京东四环附近送餐,三天之内被偷了两辆电动车。第二辆车被偷后,马兰无可奈何选择了报警。警察来了之后,她难以抑制自己的情绪而放声大哭。她的同事说,遭遇偷车、偷电池是常事,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两辆车被偷,马兰的确“有些倒霉”。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这样的场景:如果一个派单系统一开始设定的送单时长为50分钟,超过50分钟,骑手将面临配送费的扣除或者其他惩罚。那么,正常的逻辑应该是骑手会提早一点到达,例如他们会花费45分钟或者更少的时间把餐品送到。在后台的数据统计中,我们会发现大部分骑手的配送时间都低于 50分钟。当这些数据被“投喂”给算法后,它发现大多数骑手的配送耗时都低于50分钟。于是,它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把配送时间由50分钟改为45分钟。当配送时间变为45分钟后,骑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惩罚,仍旧会提早一点送达。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个人机交互的“有趣”矛盾:算法不断缩减配送时间,骑手不得不越跑越快,于是就出现了“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恶性循环。
这是我好几个月的工钱。那天我在写字楼送餐,进去(写字楼)之前上锁了。坐电梯上去,送了餐。正在走廊上走,手机上我装的GPS警报响了。当时我在20层。跑下来,车没了。应该是把车头上的线剪了,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