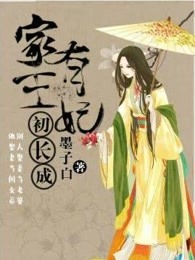张小满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父母如期出发。送他们去车站的路上,母亲一边说希望姑姑的病能好,一切平安无恙,一边又说要提前给姑姑”准备东西”,要买厚厚的棉花铺在棺材下面,要让姑姑的女儿买一套体面的衣服。她陷入对过往亲人死亡的回忆中,是如此地撕裂和混乱。
在母亲的语言里,算计是有计划、聪明、会安排的意思,意味着她利用好了每一天,把整个家庭的资源与人力都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她在超级商场和政府大楼也是这样规划自己工作流程的细节。
出发前一天是周日,我带母亲去华强北逛逛。下午坐在街边休息的时候,母亲提到,老姚告诉过她,他的新工作是在华强北的电子厂做保洁领班。我建议母亲给老姚打个电话,约他见见,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电话拨过去,母亲跟老姚交流了一番,挂了电话,她告诉我,老姚今天已经提早下班回家了,等下次他来香蜜湖的时候再见面。母亲有些遗憾。
我的母亲有两个信仰,一是挣钱,二是相信可以通过供孩子读书,送孩子们走出大山。而供孩子读书也需要钱。总之,挣钱就是母亲的信仰。她灵活变通,想尽办法,能省则省,能挣则挣,一分一毫地攒钱。
父母决定7月12日动身。我给他们买了从深圳直达县城的火车票。
挣钱要专注。母亲说:“一双手只能按一个鳖,哪能按两个鳖,人只能专注一样事。”
父母回乡的计划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每当我显得好高警远,或者想鱼与熊掌兼得的时候,她就这么提醒。
母亲形容自己焦急的心情:心焦得都㩢得断。“㩢”在陕南方言中是指把一根木柴抵在膝盖上用双手折断的动作,这个动作伴随着忍耐、疼痛和断裂爆发前的煎熬。这也像是琴弦断掉的过程,在崩断前,经历了无数力量的拉扯。
在地图上搜索,从商南县城往城郊的山区腹地,便能找到我的老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整片墨绿色,那是巨大的秦岭,滑动鼠标齿轮,放大,那些像山体血管一样的线条,有些是河流,有些是公路,密密麻麻,人也依着河流和公路居住。
一晃到了7月,姑姑已经吃不了东西,眼看着状况一天天糟糕下去。
俗话说”八分山一分水一分田”,从地名就可以看出,这里不是什么经济发达之地。“沟” “村” “湾”“岭” “坡” “棚” “岩” “崖” “脑” “盘” “场” “滩” “塘” “墩”……这些都是地名里最常见的字。父母辈的婚姻关系也是围绕着这些地名展开,很少有人嫁到县城或外地,几个嫁到外地的妇女,还是因为被拐骗。在我的成长记忆里,读书、走亲戚、搭班车去县城,都要经过这些沟沟村村:东沟、文化坪、汪家岭、水井湾、梭子棚、千家岩、勒马崖、炭沟脑、吴家屋场、落马滩、芦毛塘、柳树墩……在我老家所处的位置,一条名叫”冷水河”的河流穿村而过,注入丹江。
从4月开始,全家人都被姑姑病情恶化的阴影笼罩。 那时候,母亲每天从政府大楼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跟姑姑通视频电话,在路上,在天台上,在客厅,在阳台,在她自己的房间里。她们隔着屏幕说了很多话。
2021年10月,我回到县城后,父母花了一天时间陪我回大山深处的老家。这里盛放着母亲年轻力壮时留下的物证,每一处都印证着,母亲在与生活搏力时是多么有”算计”。
2021年春天,我们得到了姑姑病重的消息。
结婚要住在新房里,这是母亲当初答应嫁给父亲的条件之一。即使在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母亲无数次责备父亲的”冷漠”,埋怨父亲不回应她喷薄的表达欲和浓烈的情感,但她仍为这座白墙灰瓦、足足两百平,屋檐笔直、屋梁有手工雕花,一度是村里最漂亮扎实的房屋而透出隐隐的得意。
然而,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朝母亲期待的方向发展。即使她总是跟我宣称,她这辈子计划中的事情一定会想办法办成。
被遗弃的房屋如同消失在时间洪流中的过去。看着仍旧完好的房子,五十三岁的母亲回顾她的过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如果是在深圳有这么大的场子该多好,哪怕只有四分之一,我的孩子也不用如此辛苦。年轻的时候,还想着老了把操场扩大,再在核桃树下盖一个洗澡间。你跟你弟估计要把老家丢了。”
面对并不稳定的环境,母亲不止一次跟我说,在政府大楼工作,让她感到被尊重,认识了不少好心人。母亲做得格外认真,她想着能一直做下去。
这座新房标志着父母年轻时新生活的开始。
几个月后,主管老姚被上级调走了,去华强北一家电子厂负责卫生清洁,他邀请母亲同去。但如同我们在职场上也会遇到的情况,领导换岗了并不意味着员工也得跟着走,母亲还是觉得政府大楼更方便,就留了下来。她说,有好几次,管理处领导去检查,表扬她的卫生做得好,她很开心。即使没有加工资,她还是感到得到了认可。这种认可,对母亲很重要。
母亲做的第一件有”算计”的事是建议父亲在农闲时间利用自己的手艺,赚取务农之外的收入。父亲的手艺是制作蒸馒头用的木制蒸笼。整个冬天父亲都在家里乒乒乓乓伐木板,测量,装订,用竹子编笼顶。腊月末,父亲会把这些蒸笼打包挑在扁担上,一头两只或三只,到几十里外的城镇去卖。在镇上卖蒸笼的钱,父亲置换成年货挑回来。至今仍留在屋檐下的那只水泥做的圆柱体火炉是某一年最值钱的年货。
保洁人手紧缺的时候,小山叔会利用中午和傍晚休闲时间打扫政府大楼的食堂,主要是拖地。打扫食堂没有额外工资,但可以免费吃和公务员一样的三餐,品类丰富。公务员们一个月900多块的餐费,每餐食物不限量,随便打多少都行。小山叔发现,其实公务员们都吃得不多,也不爱吃肉,反而是蔬菜、红薯、玉米、南瓜等素菜最受欢迎。对小山叔来说,打工管饭,这既免去了开伙做饭的麻烦,又省钱。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加班。六十一岁的小山叔来深圳前一直在建筑工地上盖房子,他盖了一栋又一栋的房子,看着房价从几千一平米涨到几万。直到有一天,他觉得站在钢管架上有些头晕眼花,差点摔下来,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干了,需要做轻松一些的工作。再说,工地上也不会再要他了。在深圳工作的女儿把小山叔带来深圳。广东的食物让小山叔感到甜蜜蜜的,一切都很甜,连馒头里都放了糖。他希望这样的好日子能持续下去。
1997年,他们把”算计”着攒下的钱用来装修房屋。对于全中国人来说,那一年的香港回归是一件大事。对于我的父母而言,把土房子刷成白房子则是最要紧的事。母亲嫁过来八年了,她实在受不了房子的粗糙和简陋。“刮风的时候呼天呼地,泥土渣子从屋头上落下来,到处都是。你出生的时候窗户没玻璃,钉着塑料纸,外面呼呼响。”母亲擅长忆苦思甜,在深圳脚都伸不直的床上,被杂物围住的小房间,母亲不觉得苦,相比年轻时住过的”呼天呼地”的房子,深圳的房子至少不漏风沙,何况还能每天挣到钱。
小山叔觉得,月季也有了咖啡的香味。
他们装修好正屋,盖好厨房,还把厨房过道左侧的厕所屋顶改成了水泥平顶,用来晾晒粮食。1997年结束,母亲拥有了村里最敞亮的一栋房子。
活动室里有两台咖啡机,每天都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过来清洗机器,一个月可以赚5000多块。小山叔觉得这工作也太好干了。但小山叔不敢用智能咖啡机,因为他听保安说,这台机器是进口的,值很多钱,用坏了赔不起。小伙子很热情,主动邀请小山叔品尝咖啡,他帮小山叔打了一杯拿铁。“尝起来涩涩的。”但此后,小山叔也没主动去打过咖啡。那是小山叔人生中第一次尝到咖啡是怎样的味道。小伙子每次来清理咖啡机,都会清出半桶咖啡渣。深棕色的碎末散发出浓浓的香味,他对小山叔说,咖啡渣是极好的花肥。小山叔把这些咖啡渣装进塑料袋,放进帆布包里。他把咖啡渣带回女儿一家的出租房,埋在阳台的月季花盆里,月季一朵朵绽放。
二十四年后,连同母亲牵头做的”大家具”,堂屋里还有一台橘色的打麦机,一台灰色磨面机,一台压面机,一架手工木制风车,一个手工大木柜,一架大木梯搭在二楼楼板上。
有一位”处长”每周三都把家庭郊游用的脏垫子带到活动室让小山叔洗,洗完了还让拍照反馈,确保洗干净了。后面有几次,小山叔不发照片了,“处长”就没再提出这种过分要求。“洗是小事,感觉没被信任”小山叔说。
这个艳阳高照的秋日,我同母亲一起沉入对过去的回忆。每一个物件都提醒母亲和我,我们曾如此扎实地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度过了十几个春夏秋冬。在田园消逝之前,我曾感受过短暂得像羽毛一样,有光泽又能飞舞的日子,它们成为我的记忆风景,时不时在我的头脑中闪现。
常来锻炼的是几个已经退休,但在政府大楼里仍保留有办公室的”处长”。他们总是一早就来跑步,练太极拳,有时候还加人合唱团。周六的时候,常有中年女性带着孩子和瑜伽垫来,孩子在阅读,女人在练瑜伽。
在故乡,春天的开始意味着劳作开始。最先种在地里的是马铃薯,接着是玉米,接着是各类蔬菜:上海青、大白菜、娃娃菜。母亲管种菜叫”兴”菜。“兴” 这个字第一次在我的脑子里变成了有场景的动词。如果允许的话,她在深圳,最”宏伟”的计划便是在公园的空地上”兴”萝卜、“兴”白菜、“兴”黄瓜……把公园变成菜地,而不是做保洁。
母亲就是在来来回回送垃圾的路上认识了小山叔。 小山叔负责的是政府大楼活动室的卫生。活动室是用来让公务员们休息的场所,面积有上千平米。里面有健身房、图书室,还有咖啡机。活动室里人不多,小山叔主要的工作是拖地板,擦桌面、镜框及墙面上的灰尘,活儿不多,每天收集起来的垃圾一只垃圾袋都装不满。有时候,小山叔要协助活动室的管理员给图书上架,给墙上的镜框换照片。
故乡的春天里,核桃树、柳树、桃树、樱桃树、李子树、连翘树、苹果树、泡桐树、香椿树,统统开始发芽的发芽,开花的开花。在深圳,母亲形容一棵树花开得好看,常常脱口而出的赞叹是:“开得花膨膨的啊!” “膨”是爆米花炸裂时的声音,是夏天拧开可口可乐瓶盖时的声音,是拆面粉时塑料袋爆破的声音,是放学后发现父母在家时开心的心跳声。开得”花膨膨” 的那些花,在母亲眼里,仿佛是在搞舞会,那么喧闹,那么轻盈。
政府大楼的可回收垃圾不会被丢弃,而是由每层楼的保洁员分类整理,送往负三楼的地下仓库累积起来,每个月卖一次。卖垃圾所得的钱,分给大楼里的保洁员。平均下来,每个月,因为卖垃圾,每个保洁员可以多拿150块钱。这令母亲感到公平,觉得政府大楼里的管理有方法。不像在超级商场里,捡纸皮还要被惩罚。
深圳是一个四季有花的城市,“中国第一个国际花园城市”并非浪得虚名。母亲很好奇,家附近马路边花坛里的花为什么总是纷繁多样还永不凋谢?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深圳这座城市,容纳的是五湖四海的人,所以柔韧性很高。这些来这里工作的保洁员、清洁工,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却被深圳接纳了。
直到一个周末的深夜,她在和我一起散步途中,碰到了正带着二十个工人种花的湖南大叔郑江河。江河大叔五十八岁,来自常德。正在种花的工程队成员也大多来自常德,年龄最大的工人已经七十五岁。江河大叔是工程队队长,他们在深圳一个园艺公司下面工作,负责整个福田区马路花坛里花的更替,一个月工资算上加班在6000元左右。
给政府大楼扫外围广场的是保洁员里最年轻的一位。他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嘴里会一直嘀嘀咕咕,但表达不清晰,只顾低头干活,有一片树叶也会立马扫起来,像是有强迫症。后来母亲才知道,他是被老乡带过来的,可能患有自闭症之类的疾病,在老家找不到工作。
深夜马路上车少、人少,适宜工人们在路边安全开展工作。我和母亲遇到他们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半,栽花工程才刚刚开始。身着橘色马甲的工人们,手里拿着小锄头,把旧花铲起,将一棵棵”千日红”花苗栽进泥土。被铲掉的还开着紫色小碎花的”蓝花鼠尾草”变成垃圾堆在路边,有市民挑选一些品相好的捡走,带回家栽种。
我后来才知道,政府大楼这份保洁工作,即便有法定节假日仍不好招工的一大原因,是这里不包吃住。假期多,钱就相对少。很多来做保洁的老人,在乎的一是能赚多少钱,二是要包住。如若儿女不在身边,深圳的租房成本是他们承受不起的。政府大楼里一部分保洁员承包了打扫食堂的活儿,他们可以在正式员工吃完饭后在食堂用餐,一日三餐管饱。
“千日红”装在黑色筐子里,从广州郊区花圃用卡车运过来,有一万棵。一筐筐”千日红”从车厢里搬下来,一盆盆卸在花坛边,等着工人栽种。车厢腾空后,司机要符卸完的空筐子摞起来,装回车厢,带回广州。 他们要加班至凌晨才能将一万棵”千日红”栽完。
相对于其他保洁员,母亲显得热情,也相对幸运。 她和我住在一起,我承包了她生活的大部分开支,她做保洁挣的这笔钱,就能按自己的心意存起来作为养老钱。
江河大叔告诉母亲:“这些花一个多月后又会重新换一次,不等它谢就会有人打电话。”江河大叔的日常就是带着工人们在城市四处流动,在深夜种花,哪里有活儿去哪里。他做这份工作十多年了。一个月后,母亲又遇到江河大叔,这次从广州运来的是一万多棵绣球,花坛又一次穿上新衣——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为这座超级城市创造一种”整整齐齐”的美。
母亲认为老姚是一个勤快的主管,有时候甚至有点主次不分了。他从不偷懒,人手不够的时候,很多活儿他都亲自上手干,多赚一点儿。也由于一天到晚都忙于多干活多挣钱,老姚并没有太多精力去管其他人。因此,每天早上打完卡,分配完任务,各自回到清洁岗位后,基本就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保洁员们,给他们安排一些其他的活儿。管理处的经理也很少去找保洁员麻烦,开早会的时候总是对他们说,你们辛苦了,只要干好自己的岗位,将来会帮忙争取给保洁员加工资。在这份工作里,母亲感到了信任。
在老家乡村,花就是兀自长在山上、路边、田边、河边……花开花谢,顺应四季。即使是在县城,母亲也没有找到走出几百米就可以看花的地方。“深圳真有钱,这些花都是钱买来的。没想到种花也能挣钱。”母亲对买来的”花园” 一样感到喜悦。在深圳,母亲最快乐的一个际遇便是,怎么到冬天了,街道两边还是”花膨膨”的!那些盛开似樱花的异木棉像是不知道季节。
作为清洁工主管的老姚,已经五十八岁了。他一个人在深圳打工,老婆在湖北老家带孙子,还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在老家需要接济赡养。他的好脾气常被其他保洁员拿来调侃或取笑,但他依旧乐呵呵的。保洁员们对他的评价是:老姚是一个好人。
而母亲在大山深处经历的冬天总是伴随着大雪。我小时候上学,要穿过一段竹林,才能去到学校。每到下大雪时,早晨,母亲推开门,发现门被大雪封住。往往这时,竹林里的竹子已被雪压弯,东倒西歪趴在小路上,挡住前去的路。母亲会拿起一把镰刀,或者找一根长竹竿,将一棵棵落满雪的竹子扶起来。此时,地上已是齐膝深的雪了,踩起来软软的。我常想象是踩在白砂糖上,很放肆,有时会抓一把雪,冰凉的雪碰到舌尖即融。天晴的时候,空气是清冽且干燥的,阳光荒凉得让人惶然,晒到五六点才落山。白日将尽未尽之时,枯黄色太阳照着房前屋后,像是永远也不会落下去。太阳落下去后,黎明又仿佛忘记到来。黑暗的夜空,黑暗的山,黑暗的村子,无尽的黑暗,令人束手无策的黑暗,黑暗像蛇一样在膨胀了的时间中爬行。
她的大部分工资用来接济儿女,一部分存着,和老乡们合租在附近小区,一个月租金1000元左右。云南阿姨有着和母亲差不多的口头禅:老了,挣点钱自己花,帮不了儿女,也不能拖累儿女。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云南阿姨是母亲遇到的唯一一位在深圳自己交社保,老后有希望拿到退休金的保洁员。
在黑暗中,我总喜欢跟母亲挤在一张床上。我的脚很冷,她把我冰凉的脚拉过去,放在她柔软的肚子上。 她的肚皮热乎乎的,她用双手捂住我的脚并发出惊叹:“你的脚冻得像棱冰一样!”在深圳12月短暂的寒冷里,母亲依然会保持这个习惯。我们坐在沙发上,她把我的脚搬起来,放在她的腿上。我们挨在一起聊天,似乎曾经疏远她的女儿又回来了。
一位云南来的阿姨,比母亲大两岁,一天要上三个班。早上7点去政府大楼,做办公室清洁;中午休息时间,她要去附近一个家庭做家政,下午6点下班后,她又赶去附近一个单位给十几个人做晚饭。加起来,一个月的工资超过1万块。她一个人来深圳已经十几年了,交了社保,六十岁后可以拿退休金。前几年她当了奶奶,同乡的老人一般会选择回老家带孙子,但她不愿意,而是每个月出2000块给儿子,让儿子找保姆照顾孙子。
深圳没有雪。母亲按照二十四节气”算计”日子。 冬至那天被称作”进九”,2020年冬至,她准备了白萝卜瘦肉馅饺子,给我念了一个烂熟于她心中几十年的谚语:
实际上,母亲在政府大楼的同事们大多都要打几份工。遇上这样的”富婆”保洁阿姨,还要等到她在深圳待得足够久的未来。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河边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归一,耕牛遍地走
广东,特别是深圳和广州,被外界认为遍地是隐形富豪之地。最被人玩味的一个段子是说,在深广,如果你遇到一个保洁员腰间系着数量可观的钥匙,那他可能是家财万贯的”包租公”或”包租婆”。他们刻意低调收敛财力,踏实本分地劳作。此类故事组成了外地人对广东的富庶想象之一。
在故乡”不出手”的”进九”天,深圳的气温是16.2摄氏度。她终于不用穿那条穿上就让她几乎无法迈步的棉裤了,她那条有些僵硬的腿,也不再用毛巾层层包裹。
闲聊时我问母亲,在政府大楼的时候,对公务员整体是什么印象?母亲说,她没有遇到过一个正在怀孕的年轻女性,也”没有一个胖子,他们都很友善,没有戾气”。